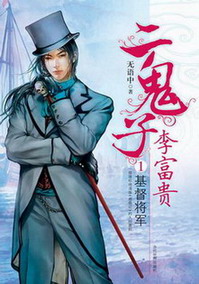鬼子进村-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战时的一些微小环节,像战前下达命令时,要考虑各位指挥官的具体情况,不同性格,有的交待任务要具体细致,有的则不必多说;在作战过程中,对那种默默实干,不喜汇报的军官率领的部队,应注意查询,否则“则有濒临危机之虞。”战后,应及时到医院慰问伤员。等等。
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既能考虑全局,又很注意细节的劲敌。
冈村宁次是很好战的,这与日军的作战风格是一致的。有专家在论及日本陆军的作战风格时,说:“日军作战的一贯长处是:决策大胆,进攻十分主动而坚决,步兵的行动顽强而又带有狂热精神。”冈村宁次身上即充满了这种“顽强而又带
冈村宁次(3)
有狂热精神”的味道。抗战初期在武汉等地作战时,冈村宁次面对数量上占优势的国民党军,仍能取胜,这固然是因为国民党军指挥失当,素质低下,但也确与冈村宁次主动、顽强的进攻精神有关。
冈村宁次在指挥上是很大胆,敢冒险的。他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时,曾主张进攻西安和延安,摧毁中国抗日中坚共产党的总部,并压迫重庆,妄想一举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他任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时,又提出进攻中国政府所在地重庆。他在给部下讲述所谓“统帅思想”时,特别提出的一条就是“大胆果敢,确信必胜。”认为过于慎重,不敢冒险的指挥官,在对华作战中,不会有多大战果。而另一方面,冈村宁次却又十分谨慎小心,并注意深入一线,接触实际。他说:“到任后或大战前后,都要首先巡视第一线兵团,这是我的信条之一。”仅到一线兵团还不行,冈村宁次还一定要找下级军官甚至士兵谈话,他说:“我一向主张每次访问前线部队,一定要听取军官、下士官以及士兵的实战经验。”冈村宁次讲,他“从任北满第二师团长,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时起,便乐于到现场倾听下级指挥官、士官、士兵讲述战斗情况,并予以鼓励,至成习惯。”“否则便很不舒心。”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后,仅一年,“便对所辖的华北蒙疆地区大致巡视一遍。”这样,就使得冈村宁次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从而制订作战计划时较少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彭德怀注意到冈村宁次这一特点,指出: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说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地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既积极主动,又谨小慎微的对手。
正如彭德怀所评价的,冈村宁次“不出风头,不多说话”,是个挺内向的人。他自己讲,他的爱好是“饮酒、读书、下围棋及钓鱼。”据他的部下讲,他常“翻阅高级综合杂志”,写生画画得也不错。这也都是些内向的人的爱好。冈村宁次曾“认为自己适于搞情报,”做些不声不响的工作,不喜欢抛头露面。
或许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些爱好吧,因而他“不粗暴”,也不像有些日军将领那样难以相处。用中国的老话讲,此人是很懂得忍而不发的吧。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坐得住,也放得下架子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不言不语,实际工于心计的人,真是个令人难以琢磨的敌手。对冈村宁次这个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中国抗日军民对他是恨之入骨的。在冈村宁次的回忆录里,他自己提到,抗战胜利后,
“在延安发表的战犯名单约二万多人,我被指定为第一号战犯,第二号战犯为曾任华北方面军的多田骏大将,第三号战犯为曾驻山东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中康中将。”冈村宁次说,中共方面始终抓住他不放,“中共方面坚决主张把我定为第一号战犯,直到1949年初与李宗仁谈判时,还要求将我引渡共方,作为谈判的一项条件。在我回国以后,至今仍不断看到报纸上对我的责难和攻击。”冈村宁次对中共方面“不依不饶”的态度,对自己“荣登榜首”的事实,很有些“委屈”和不解,他说:在当地对我个人的战犯问题,是从1945年12月初提出的。然而关于战犯问题中国方面特别重视战争中日军的暴行,其中重大事件有南京战斗等四处。我虽始终在中国战线工作,幸运的是这四处的战斗均与我无关。在冈村宁次看来,他这么一个致力于“日华提携”的人,他这么一个有着许多高雅爱好的人,怎么成了头号战犯了呢?下面,我们先不去引用当年起诉书中的文字和数据,也暂且承认冈村宁次在1937年没有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我们就从冈村宁次自供由他一手策划和指挥的冀中“五一”大“扫荡”看一看,他还有什么“委屈”可讲,还有什么道理可说。
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城市犯下的罪行,那么,“五一”大“扫荡”,则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乡村欠下的血债。
可就是这么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还偏偏有那么一些中国人对他深表同情和理解。冈村宁次说:“战争结束后,据由重庆来南京的旧友透露,重庆方面一些我的友人,都为我庆幸。”
据冈村宁次的日记,1945年12月18日蒋介石来到南京,仅过了5天,也即12月23日,蒋就迫不及待地会见了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谈话要点:蒋:您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我:深感厚情,生活满好。
蒋: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的情况,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我: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我:完全同感。
冈村宁次说,“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和蔼近人。他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这不像是一个战胜国元首与一个敌国败军之将之间的会见,倒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的重逢。
冈村宁次(4)
可能就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么多的旧友吧,最后,他竟然逃脱了中国人民的审讯,社会正义的法庭,回到了日本。
日本人,特别是冈村宁次的部下,对他则是大加赞美,极力吹捧。说他“在统率及作战方面都是罕见的名将。”是“兼备明智、卓见、果断、意志坚强等优秀品质”的人才。说他“最后成为百万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乃是理所当然。可惜为时过晚,实为遗憾。”冈村宁次,真的是如他的部下所言,是个如此完美,如此出色的“名将”、“天才”吗?当然不是。首先,冈村宁次在作战上也无法摆脱日军那一套陈旧而机械的教育方法,在指挥上决非像他的部下吹嘘的那样指挥若定,料敌如神。就是在冈村宁次颇为自得的武汉会战中,他的指挥也屡屡出现重大失策,以致参加过武汉会战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起当年的战况时,竟发出“不知畑俊六和冈村宁次当时是怎样想的”感慨。
其次,冈村宁次在为人上,也有虚伪、冷酷、不敢面对现实的一面。
冈村宁次自称是极其关心日军军风纪的,声称要“勿蹈南京事件之覆辙,”为日本军队“掠夺、强奸、放火的情况很普遍而感到叹惜。”他甚至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套“从中国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当地的治安情况的好坏(也包括日本兵的军纪)”的“理论”:绝对见不到姑娘们的踪影。系惧怕日本兵的佐证。治安不好。
对我们的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而远远地从窗口眺望,治安稍好。
在上项情况下,走出家门口眺望,中国姑娘神态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治安良好。冈村宁次这一套“理论”,倒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那么既然如此,在这位如此关心军纪,而又大权独揽的司令官先生的统率下,至少华北日军的军纪应该是有所改善吧。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日军,在冀中是怎么样的“军纪”,给冀中妇女带来的是怎样的苦痛。冈村宁次为人十分冷酷,不择手段。他自己在回忆录中说:
日军设在中国的“慰安所”
昔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战争,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两、三起强奸案,我作为派遣军参谋副长曾仿效当地海军,请求长崎县知事召募“慰安妇团”,其后强奸案未再出现,令人感到欣慰。现在(指1938年——引者注)几乎各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已形成兵站的一个分队。原来,冈村宁次还是名声狼藉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为了解决军队士兵的性饥渴,甚至可以牺牲本国妇女的自尊,多么冷酷无情。
如果说冈村宁次对他对本国妇女犯下的罪行还有那么一点内疚的话,那么,他对于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简直连一丝悔恨也没有,而且不仅没有悔恨,甚至还死不认账,颠倒黑白。在他的回忆录里,专门有一段谈到“三光”
政策,他说:这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后,几经思考,于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顺便提一句,日、中的共产党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烧、可抢、可杀的三光政策”大肆宣传。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日本进步学者的著作中也引用了这种宣传。因纯属无稽之谈,毋庸置辩。
鬼子出村(1)
冈村宁次说是“毋庸置辩”,其实还是辩了。只是他觉得有些话从自己口中说出来或许不那么方便,便借用了“原中国派遣军所属师团长船引正之”的话来替自己狡辩。这位师团长的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岩波书店出版的《昭和史》中载有:“冈村宁次大将率领的华北方面军于1941、1942年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施行了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的残酷战术——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竟然生搬一方面的史料,并煞有介事地予以发表,实为可笑。再说,这个三光政策与事实完全相反。(中略)冈村大将新阵前训的第一项便是“戒烧、戒淫、戒杀”三戒,这点我记忆犹新。每天至少在点名时听到一次列队高呼“戒烧、戒淫、戒杀”之声。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大“扫荡”中执行了“三光”政策,这是每一个敢于正视历史的人公认的事实,本来也是“毋庸置辩”的。可既然这些当年的司令官、师团长们硬是闭着眼睛说什么“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我们也只好多说几句。为了不“生搬一方面的史料”,我们就不用中国方面的史料,而用日本方面的史料来证实这一事实。一位冈村宁次当年的部下,独立步兵第42大队士兵三神高,在一篇题为“试胆——抓住农民,簇拥而上,刺成蜂窝”的文章里写道,1942年8月上旬,当他所在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