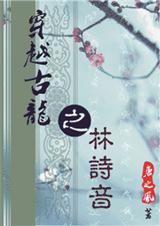小城遗事之林文-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第一卷
………………………………
引子
这个故事大概是真的,因为是一位很严肃的学长告诉我的。学长讲出来的时候,周围虽有几人,但大都心不在焉,还记得这个故事的,怕是只有我一个人了。当时的情形,学长看在眼里,便把一篇手记交给了我,其意如何,自然明白。
所以,根据学长的手记,我写下了这段文字,希望它能被更多人知晓,至少,也要使自己更长久地记住它。
在切入正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感同身受。当然,就算无法有所感触,想来也定是鄙人的文笔问题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一座小城,没错,它离我们很近,甚至于就在我们眼前。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有的似乎只是美好,好像所有人都没有烦恼,都活得很幸福。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小城,似乎只能是宁静、祥和、安谧的,小城里的学生,似乎都是无忧无虑、活泼开朗的,好像并不会有什么值得“感同身受”的事。
但是,偏偏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就有这么一座小城,叫竹溪,它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虽然表面上是那样没错。在这座小城里,就有这么一个学生,叫林文,他也不像每天七点到七点半或是其他时候媒体报道的那样——表面看来亦是如此。竹溪,林文,前者普通而鲜为人知,后者更是个普通得不为人知的名字,在此普通之地,在此普通之人身上,上演着的,也只是寻常的事而已。所以,普天之下,大概有很多人,都和这位林文一样,只是不自知罢了。
叫竹溪的小城,应该不止一座;叫林文的人,又何止万数。据学长说,这竹溪,乃在中国中部偏南,具体省份也无从知晓;这位林文,生卒年也不详,只知道是个零零后,大约生于2001年,甚至而今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他留在这世上的,似乎只有几篇文章和几首诗词。其中有一首,通篇白话,却也是最难解的;若不知道具体事迹,怕是没有人知晓它什么意思:
书行远远乡,强欲寄高堂。
结游傍佳树,独步倚危墙。
诚感治府易,佯观割麦忙。
候音未至久,不复少年郎。
那么,在这位少年郎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又为何要将这些事称为“遗事”,看了后文,应该就能明白了;只是——。
竹溪,到底在哪儿啊?
………………………………
第一章 幼年
那大约是2001年的一天,下午三时左右。
竹溪县医院的产房里,多了一位早产的准母亲,以及一位在门口等待着的准父亲。周围一片嘈杂,似乎充斥着医院来来往往的整个世界。
突然,产房里一声婴儿的啼哭盖过了所有的喧闹,林大生眼圈红了,咬紧牙关,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却仍流下了不知是欣喜还是悲楚的泪水。
产房的门打开了,一个护士抱着孩子走了出来,四下张望着:“林大生,你老婆生了!”
林大生忙擦擦眼泪,接过孩子,谢过了护士。正欲细看,护士却又将孩子抱了过去:“这孩子还得先由医院看护着,你先去看看老婆吧。”
林大生连连点头,望着孩子远去,这才想起产房里的妻子,忙快步走了进去,单膝跪在床前问道:“月娥,你怎么样?没事吧?”
秦月娥虚弱地点点头,问他:“看过那孩子,像你还是像我?”
林大生笑着撒了个谎:“都像,都像。”
秦月娥也笑了笑,又想起一件事来:“你给孩子起个名吧,叫啥都行。”
林大生脸红了:“我哪会起名啊?”自然,他早就想好了。
秦月娥还是看着他,不说话。
林大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就叫林文吧,以后有文化,长大了才有出息。”他顿了顿,又低下了头:“别像我一样……”
秦月娥抬起一只手,又放下了。两人都没再说话,但林文这个寓意深远的名字,却已经取定了,且将会伴随这个孩子的一生,或是前半生。
就像林大生自己说的那样,他没读过什么书,没有文化,平日里非常羡慕那些读书人。而秦月娥,大约是九一级的初中生,在这座小城里,本可寻个好差事,嫁个体面人。奈何命运弄人,毕业后一两月就患了眼疾,险些丧命,几年后情况才减轻,但仍时有发作。母亲托人相亲,倒相中了家境一般、忠厚老实的林大生。两人成婚后,秦月娥从娘家借来本钱,让林大生拿去做生意。林大生不懂生意经,她便让他专管跑腿干活,自己负责交际谈价钱,两人一起管账。两年下来,收入倒不少,林大生也学到了很多,于是交际开始由两人共同负责。就在第三年,秦月娥怀孕,八个月后早产,生下了林文。
秦月娥以为,林大生之所以给孩子起这个名字,真的就像他说的那样。只是,起这名字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恐怕只有林大生自己才知道了。他不明说,秦月娥也只有自个意会,就理解成了这般意思。
于是,她从坐完月子起,就把之前学过的那一点东西,再温习了一遍。等到林文三岁时,就开始教他识字,就这样一直到小学毕业,把自己脑子里所有的知识都教给了孩子。
当然,家教重要,上学更重要。林大生不懂县里学校的好坏,秦月娥却晓得。幼儿园就算了,上小学时,她就让丈夫托人找关系,把林文送进城里最好的学校——竹溪一小。这所学校据说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执教的都是些老教师,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秦月娥想着,再怎么说,自她读书时到现在,也不过二十多年,学校是不会有大变的,把孩子送进去,错不了。林大生见妻子这般有信心,也就把林文送了进去,让他在那里度过六年的小学生涯。
秦月娥的想法,在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甚至是五年前,都没错。但四年前,这所学校还真有了大变。所谓竹溪一小,有一小,自然就有二小、三小、四小,这秦月娥是知道的。但她却不知道,在十四年前,也就是她还在养病的时候,县里还有过五、六、七小,都是县上领导一时兴起兴办的,让很多闲居在家的知识分子有了就业机会。自然,师资是没有得到保证的,还没送走几届学生,就没人去读了。领导傻了眼,学校是办不下去了,可也不能让这么多人失业,就有人出了损主意,把这几所和另外几所合并一下,还能凑合办下去。就这样,一、二、三小光荣牺牲了,只有四小幸免于难。那时秦月娥正忙着教孩子,没空关心这些事,而时间一长,也就没人提起,她自然也就不知道了。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读者看到这儿可能觉得有些奇怪了:前面说了主人公是林文,怎么尽说他爸他妈呢?别急,这一千来字的前缀还是必要的,现在就把视角转向我们幼小的林文小朋友。
林文此时年纪尚小,父母的意思,他也不明白。他也和很多小孩一样,喜欢吃糖人,永远也吃不够。他也像所有的小孩子一样,淘气,爱玩,也有一帮同玩的小伙伴。整天也会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街边撵黄狗,工地玩泥巴,一群小土匪就差上房揭瓦了。别的孩子都会玩到尽兴,他也想,只是母亲总会准时找来,把他带回去上课,他也只能恋恋不舍地回去了。
林文记得,第一次母亲来找他,他不肯回去,秦月娥便好言抚慰道:“阿文乖,妈妈带你回去,路上买糖人吃。以后都要跟着妈妈回家哦。”他点点头,跟着母亲回家了。
第二次,母亲找他回家,他还是不肯。这回可没有糖人了,秦月娥只说了句“乖,回家了”,就抱着他回了家。他趴在母亲肩上,望着仍在玩耍的伙伴们,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毕竟年幼,那一点点滋味,很快就被家里的晚饭给冲散了。
第三次,母亲又找来了,他看着伙伴们,又想要糖人,便耍赖不回去。秦月娥却板起了脸,沉着声道:“回去。”他摇摇头,秦月娥便伸出手,在他屁股上打了一下,虽说不重,可毕竟才三四岁,又是第一次挨打,林文不由得“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秦月娥心软,还是拍拍他的头,说:“走,妈妈带你去吃糖人。”他却止不住,由母亲领着,一路哭着去了。
当然,自那以后,林文便知道该跟着母亲回去了。只是从那时起,秦月娥买的糖人也少了些,大概是不想让孩子小时就浸在甜里。至于林文,还是该玩就玩,该上课时才上课,倒也算是无忧无虑,悠哉悠哉,自在快活。。
就这样过了四年,林文七岁了,也该上小学了。正如前文所说,他要被送进秦月娥眼中最好的竹溪一小就读。他的故事,也从现在才正式开始。
………………………………
第二章 进学
“竹溪一小。”开学前一天报名时,林文看着校门上这四个字,小声念了出来。
秦月娥也看着校门,轻声对他说:“阿文,从今天起,你就要在这里念书了。这可是全县最好的小学,你可得用功啊。”
林文眨巴眨巴眼,天真地问道:“妈妈,那最好的中学呢?”
秦月娥一愣,随即笑道:“等你好好念完小学,就可以去最好的中学啦。”林文点了点头,便牵着母亲的手,走进了学校。
林文不知道,自己刚才问的那句话分量有多重。大概就是从这时起,秦月娥意识到了一点:小城终究只是小城,要想孩子有出息,还得送到大城市去。在之后的几年里,她一直坚定着这个想法。当然此时,她还得带林文去报名。
到了班上,见到了班主任,秦月娥抢着到跟前问:“老师,请问您贵姓?”
班主任抬了抬头:“免贵,姓何。”
秦月娥便陪着笑脸道:“何老师啊,我是咱班上林文的家长,孩子小,不懂事,还请老师平日里多关照一下。”
大概很多家长都提过这个要求,何老师也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会意。秦月娥明白这个态度,便也不再提。交完杂费,就带着林文回去了。
第二天,才是正式开学的日子。林文早早起了床,走了两里路到了学校。进了教室,何老师已在班上了。林文怕生,不敢打招呼,又想起早上母亲叮嘱的话,只得大着胆子走了过去:“何老师好!”
何老师抬起头来,打量着面前的这个学生。见对方看过来,林文条件反射地笑了笑。那笑容很奇怪,它既不像普通小学生该有的天真烂漫的笑,也不像成年人大方的微笑,更不像老年人慈祥的笑。它就像是挤牙膏一样被挤出来的那种,但又不像《百万英镑》里那样复杂的笑。这个笑,还是单纯的,用三个字来概括叫不自然,用俩字来形容,就叫怯懦。
何老师后来追忆往事时,也忆起了林文的这个笑容。据他说,这样的学生,他见过的也不少,便也没在意。却没想到,这孩子后来成了那样。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认真对待此事。只是后来,到底已是后来了,再怎么后悔,都于事无补。
且说此时何老师看在眼里,也没放在心上,还是点点头;“去找个座位坐下吧。”
林文“嗯”了一声,便跑到教室中间,找了个位子坐下,就从包里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