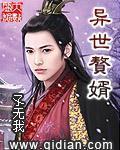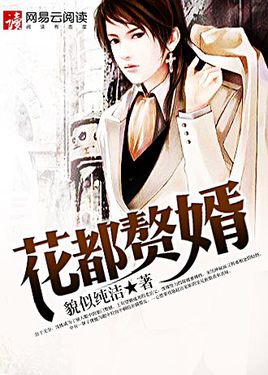赘婿-第8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巴拉巴拉巴拉,你们会觉得回到了课堂上,实际上,这不过是文学的入门知识而已。
书到底是为什么而写呢?至少我不是为了让读者学会古代的排兵布阵。
人们看书各有侧重点,这很正常,这里说这些,只是为了表达,因为这样的原因,我选择了我的写作方式。即便我写作之前参考过一些排兵布阵,自己脑子里也过过一遍,写的时候,我仍旧不会刻意去交代它,因为没有意义。起点也有很多战争文,有我喜欢的,但从头到尾,我没有从哪本书的排兵布阵里感到过乐趣,如果是专为“我很懂打仗”这种感觉而来的读者,只好放下这本书了,因为我确实不写它。
对于战争描写,解释到这里。
第八集是承上启下的一集,整个剧情的走向是有些快的,接下来整本书可能还有三集左右的篇幅,希望每集最多九个月,不要超过太多。
我曾经说过,到目前为止,我的每本书都是练笔,究其原因,我能清楚地看到那个完美的高点在哪里,我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缺点,看到下一步该迈的地方,如何去抵达最终的目标。因为这个,练笔会一直持续。
在赘婿这本书的开端,我用了相对繁复的笔调,相对复杂甚至于接近臃肿的表达文字来尽量细致地写一些东西,是有其目的性的。在《异化》的后两集里,我了解和掌握到起承转合对情绪表达的作用,掌握到许多微小情绪和暗示的作用,赘婿开端的时候,我开始了对情绪表达的深挖。就好像一种情绪,譬如说爽点吧,最初我可以写到八分,当我触及十分这个深度的时候,要达到它,我可能需要两倍以上的描述,需要反复的利用不同的手法去表达它,只有经过反复的挖掘,才能将这些东西真正的吃透。
因此,赘婿的开头,有些人看完之后,说平淡,实际却不是的,每一章里埋藏的伏笔、暗示、勾动人心使人欲罢不能的东西,可能比很多人十几章里埋得还要多。
这种不在乎文字的使用量,执拗地要达到表述深度的训练,在赘婿结束第七集的时候,基本上也就完结了。
第八集里,面对新一轮的训练目标,进行了一些尝试,到这一集完成,才真正确定了目标。接下来,已经可以开始修剪文笔中的枝节,在先前的许多表述中,为了把握住一瞬即逝的灵感以及追求淋漓尽致的效果,我有着不遵循正规语法而纯凭第一印象捕捉词句的习惯,接下来也需要进行一定的凝练。至于情绪,第七集过后,看来已不必追求十二分的挖掘,有些地方,可以开始留下余韵。
这一轮的练笔,可能会持续到整本书的完结。
当然,这是我在自我写作上的调整,可能跟读者关系不大,也只是趁着小结的机会做出系统性的梳理,剧情走向不会因为练笔而失控,这个可以放心,很可能大家也不会感受到太多的差别。
许多人并不能明白我为什么写得慢,最近偶尔也看到类似于“这样的一章为什么要那么久”的问题,老读者大多不再问了,对新读者,可以说点新情况。
一本传统,写到最多,几十万字百万字顶天,一堆线索由起承转合到最后的归纳,也只是几十万字的量。网络写到几百万字,一开始看似可以取巧,但如果仍旧追求起承转合的圆融,线索收放的自然,到现在,已经是比传统高几倍到十几倍的工作量。
在这本的开头,放下一条线,写出来一个情节,我可以随手放,只要脑子里随便留点印象,将来有一天,顺手收起来就行了。然而到了几百万字以后,每放一条线,我都得清楚地看到它怎么收,如何跟其它的线索穿插起来,每写一个情节,故事的结尾都要在我的脑子里过一遍。
网络一开始看起来是占了便宜,但如果真的把一本“写好”的标准拿过来,到最后是谁也无法取巧的水磨工夫。网络要一个好结尾,比写一个好开头,艰难几十倍。
我将这个作为网络的最后进阶来看,如果真的能够另一个结尾到达升华,把每一条线都放好,那么距离一本哪怕是传统意义上的完成体,就只剩下了最后三遍的细节修编了——但这些改错别字的工作是无所谓的,所以到这里就基本能够交代了。
写一个情节,把结尾在脑子里过好几遍,构思必须走通,不能心存侥幸,这里没有任何捷径了。这本书还剩最后的三集,卡文可能仍旧是寻常的事情,但是,不写好它,我还能怎么样呢?我已经放进去五年的时间了。
哪怕更新不稳定,无聊的时候当然还是会求月票,当然,眼下的起点跟以前不同,作者可以发红包收月票,我就不过多参与这个事情了,月票只是个游戏,我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多,会更有面子嘛,但如果是手上钱不多的读者,不妨去把月票投给他们,拿了起点币来订阅我的书,足感盛情。
第八集整理一下,也就是这些东西。
欢迎进入赘婿第九集:《辽阔的大地》
(秦失其鹿——《史记》)。
第七二〇章 少年初见江湖路()
夜空上是流淌的银河。
夜色下,偏僻贫瘠的小山和村庄,村庄老旧,房舍院落虽不多,但处处可见人活动留下的痕迹,显然村人已在此生活许久。山坡上一间寺庙则显然是新砌起来的事物,红瓦黄墙,在这荒僻的山村间,是不容易见到的颜色。
子夜时分,一道身影摇摇晃晃地从山林里出来了,一路朝那寺庙的方向过去。他的步伐虚弱无力,行走之中,还在山坡上的茅草里摔了一跤,随即又爬起来,悄然前行。
这是一名半身染血、衣衫褴褛的少年人,脚下的草鞋破旧,鲜血结痂后的头发也乱如蒿草,一双眼睛里没有太多的神采,看来与这乡野山间随处可见的村人也并无多大区别。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腰间悬着一把破刀,刀虽破旧,却显然是用于劈砍杀人的武者之刀。
少年人悄然接近了寺庙,脚步和身形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他在院墙外摸索了片刻,然后悄然翻了进去。
世道已乱,庙宇之中也并非全无警戒,只是与好应付的乡人打惯了交道,守夜的僧人早在屋檐下打起盹来,少年摸索着过去,犹豫了片刻,然后直扑而上!
破旧的刀子朝着僧人的脖子割下去,少年用尽全身力气将那和尚的嘴按住,将他压在台阶上。片刻之后,和尚不动了,血腥的气息弥漫开来。
少年便朝着院子里的第一间房子摸过去,他挑开了门闩,潜行而入。房间里两张床,睡着的和尚打着呼噜,少年人籍着微光看见那和尚的脖子,一手持刀柄一手按刀背,切将下去,再用整个身体压上,夜里传来些许挣扎,不久之后,少年往另外一张床边摸去……
天空上星河流淌,星空下的寺庙之中,少年脚步踉跄的连杀了几个房间的和尚。到得后头几个房间时,才终于闹出了动静,打斗声在房间里响起来,一名胖和尚衣衫不整撞门而出,他手中****一根棒子,叫了几声,但小小院落里守夜和尚的鲜血早已溢出一大滩。
后方少年冲出,手中还是那把破刀,目光凶戾形如疯虎,扑将上来。胖和尚持棒迎上,他的武艺力道均比那少年为高,然而这样单对单的生死搏杀,却往往并不由此定输赢,双方才交手两招,少年被一棒打在头上,那胖和尚还不及高兴,踉跄几步,低头时却已发现胸腹间被劈了一刀。
胖和尚平日练武,也不是未有杀过人,然而群殴与放对终究不同,他原本自持武艺必能杀了对方,精神紧张间却连胸口中刀都未觉得疼痛,此时一看,顿时愣在了那里。少年已再度冲上来,照着他头脸劈了一道才又迅速跑开,绕到和尚身后又是一刀,胖和尚倒在地上,片刻间便没了呼吸。
那胖和尚的房间里这时候又有人出来,却是个披了衣裳睡眼朦胧的女人。这年月的人多有夜盲症,揉了眼睛,才籍着光芒将外间的情形看清楚,她一声尖叫,少年冲将过来,便将她劈倒了。
另一个房间里又传出响动。少年神色焦躁起来,冲过去踢开门,看了一眼,房间里有女人的声音响起,有女人叫了一声:“狗子!”这名叫狗子的少年人却知道寺中若再有和尚他便必死无疑,他去开了寺庙里剩下的一扇门,待看见那房间里没人时,才微微松了一口气,原来方才那胖和尚,就是这庙里最后一个男人了。
先前的房间里有两个女人冲出来,看见了他,尖叫着便要跑。少年回过头来,他先前头脸间便多是血迹,方才又被打了一棒,此时血流满面,犹如恶鬼罗刹,两个女人尖叫,少年便追上去,在庙门处杀了身形稍高一人。另一人身形矮小,却是名十四五岁的少女,跑得很快,少年从后方将刀子掷出,打中那女子的腿,才将对方打得翻跌在草丛。
这少女在草丛里爬,看见那恶鬼般的少年跑近了,哭着喊:“狗子,你莫杀我、你莫杀我,我们一起长大,我给你当婆娘、我给你当婆娘……”那少年走过来,张开嘴低吼了几声,似在犹豫,但终于还是一刀劈在了少女的头上,将她劈死在草丛里了。
将这最后一人劈死后,少年瘫坐在草丛里,怔怔地坐了一阵后,又摇摇晃晃地起来,往那寺庙回去。这小小寺庙正殿里还燃着香烛,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在这修罗场中静静地坐着。少年在各个房间里翻箱倒柜,找出些米粮来,然后巴拉出柴火铁锅,煮了一锅米饭。煮饭的时间里,他又将寺庙各处搜罗了一番,找出金银、吃食、伤药来,在院落里擦洗了伤口,将伤药倒在伤口上,一个人为自己包扎。
药触到伤口上时,少年在院子里发出野兽一般的嘶吼声。
过得一阵,饭也好了,他将烧得有些焦的饭食拿到院子里吃,一面吃,一面抑制不住地哭出来,眼泪一粒粒地掉在米饭上,然后又被他用手抓着吃进腹中。夜晚漫长,村子里的人们还不知道山上的庙宇中发生了此等惨案,少年在寺庙中寻到了不多的金银,一袋小米,又寻到一把新的尖刀,与那旧刀一同挂了,才离开这里,朝山的另一边走去。
夜色渐开,少年翻山越岭,走出了十余里,太阳便渐渐的炽烈起来。他疲累与伤痛加身,在山间找了处阴凉地睡下,到得下午时分,便听得外间传来声音,少年爬起身来,到山林边缘看了一眼,不远处有看似搜寻的乡人往这边来,少年便连忙启程,往林野难行处逃。这一路再走了十余里,估摸着自己离开了搜寻的范围,眼前已经是崎岖而荒凉的陌生林野。
这位杀人的少年小名狗子,大名游鸿卓。他自小在那山村中长大,随着父亲练刀不缀,俗话说穷文富武,游家刀法虽然名声不障,但由于祖辈余荫,家中在当地还算得上富户。尽管游鸿卓七岁时,女真人便已南下肆虐中原,由于那山村偏僻,游家的日子,总还算过得下去。
曾经太平的中原换了天地,小小山村也难免受到影响,抓丁的军队过来,被游家用钱财应付过去,饥荒渐临,游家有些底蕴,总还能支撑,只是大光明教过来传教时,游鸿卓的父亲却是深信了庙中和尚们的话语,不能自拔。
此时中原大地的太平年景早已远去,只能从记
![[转世·重生] 完美赘婿 作者:吴笔(起点vip2014-05-28完结)封面](http://www.beike3.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