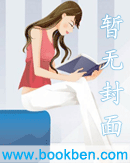克里希那穆提传-第4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64年的12月我到达马德拉斯,住在瓦桑?威哈尔。克里希那吉时常和我们共进晚餐。马哈瓦恰利、阿秋、南迪妮、巴拉宋达兰都在场。罗?萨希布没有从浦那赶来此地。晚餐后我们开始进行讨论,我问道:“心智要想突破,必须采取哪种行动?必要的探索已经做到了,自知之明的觉察力有了,眼睛睁开了,耳朵在聆听,心智也觉醒了,然而整体的觉察和慈悲还是欠缺。要想突破,必须有完整的行动才行。”克里希那吉说:“确实如此。”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应该深入讨论。
第二天晚上我们再度试着去发现那个行动是什么。克里希那吉说:“觉知和情感的活动能不能合一。”
“拥有丰富精髓的觉知是怎么产生的?”我问道。
克里希那吉说:“那必须是一种非常单纯的活动。”然后他就静默不语了。讨论的本身为这个房间制造了一种气氛。这股能量像火焰一般,燃透了意识的长廊。屋子里充满着深刻而无量的空寂。这股能量大到连身体都无法承受。我们当时围着克里希那吉盘坐,我的身体实在无法承受这股能量,只好靠墙而坐。克里希那吉挺直地端坐着,头部没有任何动作,时间好像停止了。
1963年,聚集在拉吉嘉特的友人中,有一位高大健壮、长相很好看的年轻人。他名叫艾伦?诺德,是从南非来的音乐家。他在1963年的夏天参加了克里希那吉在萨嫩举行的演讲,并且和克里希那吉见了好几次面。不久他就切断了和南非的联系。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三部分
第24章 没有创意的人才设立僵死的制度(2)
从1964年的冬天到1965年,诺德伴随着克里希那吉来到印度。不久克里希那吉就告诉我们,他想让诺德充当他的秘书,陪他一同旅行,处理他的信件往来,鼓励青年人前来聆听他的演讲,等等。
1965年的秋天以前,克里希那吉还在欧洲,诺德开始充当他的秘书;1965年10月克里希那吉回到印度,陪同他的有玛丽?津巴乐斯特、诺德和乔治?韦涛卡斯。乔治?韦涛卡斯是来自希腊的同类疗法专家,多年以后他变得非常著名。克里希那吉这回要在德里举行数场演讲,然后再到瓦拉纳西。
克里希那吉曾经寄信给马哈瓦恰利,他很天真地建议马哈瓦恰利,好好安排玛丽?津巴乐斯特、诺德、乔治?韦涛卡斯住在拉吉嘉特的校园里。马哈瓦恰利对于舒适和审美的观点都属于太古时代,因此这些访客所受的招待简直是一场灾难。
在印度,厕所永远被视为污秽的地方,传统的印度教徒每次上完厕所都得洗澡。阿秋?帕瓦尔当告诉我们,他还记得过去住在瓦拉纳西时,婆罗门外出都会多带一条多蒂腰布,因为在友人家如厕之后必须清洗身体。多年以来我一直建议马哈瓦恰利,起码的卫生设备是必要的,但是都没什么效果。对他而言,抽水马桶或洗面盆都是不必要的奢侈品。多少世纪以来,小木桶和金属做的小水罐,已经足以解决印度人的需求,因此他觉得没有什么改变的理由。60年代的拉吉嘉特校园,只有克里希那吉的屋子里装置了起码的设备。玛丽?津巴乐斯特是典型上流社会的产物,她生长在一个最考究的环境里,已经习惯于父亲和丈夫提供给她的豪华生活。如今她却被安置在一个没有抽水马桶、没有浴盆的屋子里。这间屋子的墙壁刚刚粉刷过,窗户到处都是白色的涂料。克里希那吉亲自前来探视他的客人所住的房间。他被吓坏了,发了一顿很大的脾气之后,立刻安排玛丽?津巴乐斯特搬到他住的房子。但是马哈瓦恰利仍然不为所动。
克里希那吉和马哈瓦恰利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别扭。
从60年代开始,克里希那吉对于学校、工作人员和校务的态度有了重大的转变。他要求大家不断地改革。他发现印度正在急遽衰退,学校必须从昏睡中醒来。他觉得学校不能再停滞不进,眼前看不到任何的创造力,他不断提醒基金会的成员和学校的老师:“快点动起来!如果你们还在原地踏步,你们就会衰退僵化。”他认为一个人的内心和外在的工作,都必须一直不断地进展,他在写给我们的一封信中如此说道:“既然已经进展到某种程度,就该继续前进,不该原地不动。不进则退,你们不能静止不动。”克里希那吉的组织必须有爆发性的改变,在印度,一人觉醒,连高山都会移动。
1965年的夏天,我前往格施塔德探望克里希那吉。有人送了克里希那吉一辆奔驰汽车,他带着我兜风;即使缺少练习,他在急转弯的道路上仍然开得很稳。他开车的技术真是一件令人赞叹的事。
1966年的夏天,在从美国返回印度的途中,我顺道前往格施塔德探望克里希那吉。克里希那吉告诉我,美国有许多年轻人被他的演讲吸引。诺德曾安排克里希那吉前往几所重要的大学演说。年轻人正在反抗美国现存的文化,他们渴望的是“立即涅”。接触克里希那吉令他们觉得有充电的感受,于是他们纷纷前来听讲。但是他们并不愿意过简朴而严肃的生活,他们也不想放弃各种的迷幻经验,于是他们又转向那些比较柔顺、承诺他们至乐的上师。一大群年轻人率先前来萨嫩听讲,但是其中很少有人愿意认真地探究自己,或加入克里希那吉的工作。不久萨嫩就变成东西欧严肃人士的聚集地。这些人非常关心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他们想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诺德继续陪同克里希那吉访问印度,1966年的整个冬天他们都在一起。每一次的来访,克里希那吉和马哈瓦恰利之间的关系都在恶化,克里希那吉和印度基金会的鸿沟也愈来愈深。早在欧洲时就有人告诉克里希那吉,印度基金会的成员帮着拉嘉戈帕尔反对克里希那吉,基金会显得相当自大、狭窄与自满。
回到印度他继续严肃地询问大家,他已经讲了三十年的话,为什么还没有任何进展。他拒绝拿印度和其他国家相比。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我死了怎么办?有谁能维持这些地方?”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巨大的压力在我们之中越筑越高。
当时的情况非常奇怪,这位伟大的老师总是站在讲台上热情地描述没有冲突的心智。他自己已经解脱压力,他亲近的伙伴却被他所提出的问题压得透不过气来。多年之后我们才了解克里希那吉的问题的本质,以及深刻的聆听和存疑所造成的能量。
1967年的1月,艾伦?诺德和马哈瓦恰利在瑞希山谷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克里希那吉对此事非常不安,他和我长谈,表达他的深度关切。马德拉斯的瓦桑?威哈尔好像一个死寂的地方,很少有人前来阅读或讨论。克里希那吉说:“没有创意的人才设立僵死的制度。”
那一年的冬天,诺德没有陪同克里希那吉回印度。早在1963年,克里希那吉就告诉过马哈瓦恰利,基金会的运作必须做重大的改变了。1967年的冬天,他一回到马德拉斯,便要求马哈瓦恰利与嘉洛韦分担基金会的工作。后者是一名苏格兰人,他刚刚辞去宾尼公司的总裁职位。克里希那吉又建议马哈瓦恰利接受贾亚拉克斯密的协助,共同维护瓦桑?威哈尔的房子和花园。马哈瓦恰利没有表示明确的意见。贾亚拉克斯密是南印度的依安格尔婆罗门,非常具有处理事务的才智,特别是在房地产方面,对于南印度的古典音乐也有深入的认识。60年代初期她就开始造访瓦桑?威哈尔。她深深浸淫在依安格尔婆罗门传统中,额前总是点一颗吉祥痣。她穿深绿或枣红的纱丽,按照依安格尔传统的穿法斜披在肩上。她说话轻柔,行动却很强悍。每天傍晚她都送克里希那吉到阿迪亚尔的海滩散步。
1967年对我们而言是阴郁的一年。克里希那吉显得焦躁和吹毛求疵,他的话语变化多端;你可以感觉他正进入重大的转变。1967年的2月9日,克在孟买的新教育基金会中致词,他以热切的语气叙述他对印度基金会的忧虑,我们在场的人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克里希那吉说:“我准备要说一些话,这些话没有一点批评或谴责的意味。我的心中真的没有任何评断,我希望你们从一开始就明白这点。
“我已经讲了四十五年的话。瑞希山谷和拉吉嘉特最初创立只有一个动机。这两个地方都是实践教诲的神圣场所。我希望你们不要误解这句话的意思。我想现在是算总账的时候了,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地方是否真的在实践这些教诲,能不能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可能会让人误解。我当时说的是:‘我们的学校必须成为印度的绿洲,我们必须守护它们,让它们和周遭的混乱隔离。’我真的有很强烈的感觉,而且觉得十分振奋。但是我不得不说,过了这么多年,这两个地方还是没有开花结果。
“我也许永远不再回来,也许很快就死了。我告诉马马(马哈瓦恰利),即使我回来,也只是停留一小段时间,不会像现在一待就是五个月。我的体力已经不够了,因为我的睡眠状况不太好,而且时常感到疲倦。
“你们必须考虑,我死了你们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也许不再回来,也许回来一段短暂的时间。这件事将由我全权决定,其他人是无法做主的。
“这两个地方能不能守护得好,你们了解吗?我指的不是由巴拉宋达兰或别的人来守护,使它们不至于腐化。我指的是你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守护它们,使它们成为真正的绿洲。
“今天早上我告诉基蒂吉,中饭时又告诉普普尔,我们必须很快地采取一些行动。至于该采取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大概还有十年左右。我不想浪费我的能量,我必须专注在现有的每一件事上。我现在是很清醒地、毫不感情用事地在说这些话。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守护这两个地方?请务必了解‘守护’这两个字指的是:在这个疯狂的世界,我们要把这两个地方当绿洲一样保护。还有如果我不再回来,我死了,你们该怎么办?
“四十年来我们制造了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大半生奉献给这件事,它到底有了什么进展?如果只说:我们已经尽力了!这是不够的。我并不是在论断你们的对与错,我只是在质问我们该怎么做。
“同样的事也在奥哈伊发生了。你们大概知道克里希那穆提出版公司和我之间的困扰。我们一开始想共同建立一个深刻、永恒而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奥哈伊那边也一样没有结果。
“我们该怎么办才能使这两个地方变成教诲的绿洲?我们要如何使它们变得有价值?我和马马已经为这件事讨论了许多次、许多年,现在我对自己说:我们该怎么办?”
马哈瓦恰利打断了克里希那吉的话,企图加以解释,找出一些借口,但是克里希那吉并不想听下去。
“你说的话我都了解,我们在拉吉嘉特和瑞希山谷已经为这件事讨论过无数次。我们讨论这件事已经有七年了。我想问的是,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让我们把过去忘掉,忘掉我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我们已经尽了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