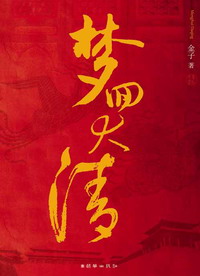大清相国-第6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安图道:“皇上批你们免一百万两,但湖南也只能蠲免七十万两,多批的三十万两交作部费。”
刘传基大吃一惊,道:“您说什么?我都弄糊涂了。”
安图没好气,说:“清清楚楚一笔账,有什么好糊涂的?你们原来那位师爷可比你明白多了。假如皇上批准湖南免税一百万两,你们就交三十万两作部费。”
刘传基问道:“也就是说,皇上越批得多,我们交作部费的银子就越多?”
安图点头道:“你的账算对了。”
刘传基性子急躁,顾不得这是在什么地方,只道:“原来是这样?我们不如只请皇上免七十万两。”
安图哼了声,说:“没有我们家老爷替你们说话,一两银子都不能免的!”
刘传基只好摇头叹道:“好吧,我回去禀报巡抚大人。”
三天之后,明珠去南书房,进门就问:“陈大人,云南王继文的折子到了没有?”
陈廷敬说:“还没见到哩,倒是收到湖南巡抚张汧的折子,请求蠲免赋税一百万两。”
明珠听着暗自吃了一惊,不相信刘传基这么快就回了趟湖南,肯定是私刻官印了。他脸上却没事似的,只接过折子,说:“湖南连年受灾,皇上都知道。只是蠲免赋税多少,我们商量一下,再奏请皇上。”
夜里,明珠让安图把刘传基叫了来。安图领着刘传基去见明珠,边走边数落道:“刘师爷,你也太不懂事了。咱家老爷忙得不行了,你还得让他见你两次!咱老爷可是从来不对人说半句重话的,这回他可真有些生气了。”
刘传基低头不语,只顾跟着走。明珠见刘传基进了书房,劈头就骂了起来:“传基呀,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呢?你竟敢私刻巡抚官印,你哪来这么大胆子?张汧会栽在你手里!”
刘传基苦脸道:“庸书只想把差事快些办好,怕迟了,皇上不批了。不得已而为之。”
明珠摇头不止,道:“你真是糊涂啊!你知道这是杀头大罪吗?事情要是让皇上知道了,张汧也会被革职查办!”
刘传基道:“庸书心想这事反正只有明相国您知道!您睁只眼闭只眼,就没事。”
明珠长叹道:“张汧是我的老朋友,我也只好如此了。皇上已经恩准,蠲免湖南赋税一百万两,你速速回湖南去吧。”
刘传基跪下,深深地叩了几个头,起身告辞。明珠又道:“传基不着急,我这里有封信,烦你带给张汧大人。”
刘传基接了信,恭敬地施过礼,退了出来。
安图照明珠吩咐送客,刘传基说:“安爷,请转告明相国,三十万两部费,我们有难处。”
安图生气道:“你不敢当着咱老爷的面说,同我说什么废话?”
刘传基道:“皇上要是只免七十万两,我们这两年一两银子也不要问老百姓要。皇上免我们一百万两,我们就得向老百姓收三十万两。哪有这个道理?”
安图道:“张汧怎么用上你这么个不懂事的幕僚!别忘了,你私刻官印,要杀头的!”
刘传基也是个有脾气的人,不理会安图,拂袖而出。
第二日,刘传基并不急着动身,约了张鹏翮喝酒。原来刘传基同张鹏翮是同年中的举人,当年在京会试认识的,很是知已,一直通着音信。张鹏翮后来中了进士,刘传基却是科场不顺,觅馆为生逍遥了几年,新近被张汧请去做了幕宾。刘传基心里有事,只顾自个儿灌酒,很快就醉了,高声说道:“明珠,他是当朝第一贪官。”
张鹏翮忙道:“刘兄,你说话轻声些,明珠耳目满京城呀!”
刘传基哪里管得住嘴巴,仍是大声说话:“我刘某无能,屡试不第,只好做个幕宾。可这幕宾不好做,得昧着良心做事!”
刘传基说着,抱着酒壶灌了起来,道:“为着巡抚大人,我在明珠面前得装孙子,可是我打心眼里瞧不起他!我回去就同巡抚大人说,三十万两部费,我们不出!”
张鹏翮陪着刘传基喝酒直到天黑,送他回了湖南会馆。从会馆出来,张鹏翮去了陈廷敬府上,把刘传基的那些话细细说了。
陈廷敬这才恍然大悟,道:“难怪朝廷同各省的文牒往来越来越慢了!”
张鹏翮道:“现如今我们言官如有奏章,也得先经明珠过目,皇上的耳朵都叫明珠给封住了!陈大人,不如我们密参明珠。”
陈廷敬道:“鲁莽行事是不成的,我们得先摸摸皇上的意思。平时密参明珠的不是没有,可皇上自有主张。”
张鹏翮摇头长叹,只道明珠遮天蔽日,论罪当死。
五十二
皇上那日在畅春园,南书房送上王继文的折子。皇上看罢折子,说:“修造大观楼,不过一万两银子,都是由大户人家自愿捐助。准了吧。”
陈廷敬领旨道:“喳!”
皇上又道:“王继文的字倒是越来越长进了。”
陈廷敬说:“回皇上,这不是王继文的字,这是云南名士阚祯兆的字。”皇上吃惊道:“就是那个曾在吴三桂手下效力的阚祯兆?”
陈廷敬道:“正是。当年吴三桂同朝廷往来的所有文牒,都出自阚祯兆之手。臣叹服他的书法,专门留意过。”
皇上叹道:“阚祯兆,可惜了。”
陈廷敬说:“阚祯兆替吴三桂效力,身不由己。毕竟当时吴三桂是朝廷封的平西王。”
皇上点点头,不多说话,继续看着折子。
明珠奏道:“启奏皇上,噶尔丹率兵三万,渡过乌伞河,准备袭击昆都伦博硕克图、车臣汗、土谢图汗,且声言将请兵于俄国,会攻喀尔喀。”
皇上长叹一声,道:“朕料噶尔丹迟早会反的,果然不出所料。”
皇上说罢下了炕,踱了几步,道:“调科尔沁、喀喇沁、翁牛沁、巴林等部,同理藩院尚书阿喇尼所部会合。另派京城八旗兵前锋二百、每佐领护军一名、汉军二百名,携炮若干,开赴阿喇尼军前听候节制。”
明珠领了旨,直道皇上圣明。皇上又道:“噶尔丹无信无义,甚是狡恶,各部不得轻敌。粮饷供给尤其要紧,着令云贵川陕等省督抚筹集粮饷,发往西宁。”
明珠领旨道:“喳,臣即刻拟旨。”
皇上沉吟半晌,又道:“徐乾学由户部转工部尚书,陈廷敬由工部转户部尚书。”
陈廷敬同徐乾学听了都觉突兀,双双跪下谢恩。
皇上道:“朕不怕同噶尔丹打仗,只怕没银子打仗。陈廷敬善于理财,你得把朕的库银弄得满满的!”
陈廷敬叩头领旨,高喊了一声喳。
陈廷敬同徐乾学择了吉日,先去工部,再到户部,交接印信及一应文书。徐乾学说:“这几年南方各省连年灾荒,皇上给有些省免了税赋;而朝廷用兵台湾,所耗甚巨。如今西北不稳,征剿噶尔丹必将动用大量钱粮。陈大人,您责任重大啊!”
陈廷敬道:“我粗略看了看各清吏司送来的文书、账目,觉着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没有钱粮上解之责的省,库银大有文章。”
徐乾学道:“陈大人这个猜测我也有过。这些省只有协饷之责,库银只需户部查点验收,不用解送到京,全由督抚支配。我到户部几个月,还没来得及过问此事。”
陈廷敬道:“大量库银全由地方支配,如果监督不力,必生贪污!”
徐乾学含含糊糊道:“有可能,有可能。”
王继文同幕僚阚祯兆、杨文启在二堂议事。杨文启说:“抚台大人,免征铜税是陈廷敬的主意,修造大观楼陈廷敬也不同意。陈廷敬真是个书呆子!”
阚祯兆却道:“抚台大人,我以为皇上准了陈大人的奏请,不征铜税,自有道理。铜税重了,百姓不肯开采,朝廷就没有铜铸钱啊。”
杨文启说:“可是没了铜税,巡抚衙门哪里弄银子去?还想修什么大观楼!”
阚祯兆道:“抚台大人,大观楼不修也罢。”
王继文听任两位幕僚争了半日,才道:“阚公,您可是我的幕宾,屁股别坐歪了呀!”
阚祯兆道:“抚台大人花钱雇我,我理应听命于您。但我做事亦有分寸,请抚台大人见谅!”
杨文启说起风凉话来,道:“同为抚台大人幕宾,阚公为人做事,却是杨某的楷模!”
王继文听出杨文启的意思,怕两人争吵起来,便道:“好了好了,两位都尽心尽力,王某感激不尽。阚公,我王某虽无刘备之贤,却也是三顾茅庐,恳请您出山,就是敬重您的才华。修造大观楼,皇上已恩准了,就不是修不修的事了,而是如何修得让皇上满意!”
阚祯兆只好道:“阚某尽力而为吧。”
王继文命人选了个好日子,携阚祯兆、杨文启及地方乡绅名士在滇池边卜选大观楼址。众人沿着滇池走了半日,处处风光绝胜,真不知选在哪里最为妥当。
王继文说:“皇上恩准我们修造大观楼,此处必为千古胜迹,选址一事,甚是要紧。”
杨文启道:“湘有岳阳楼,鄂有黄鹤楼,而今我们云南马上就有大观楼了!可喜可贺!”
乡绅名士们只道天下升平,百姓有福。阚祯兆却沉默不语,心事重重的样子。
王继文问道:“阚公,您怎么一言不发?”
阚祯兆道:“我在想筹集军饷的事。”
王继文说:“这件事我们另行商量,今日只谈大观楼卜选地址。”
阚祯兆点点头,心思仍不在此处,道:“朝廷令云南筹集粮饷军马从川陕进入西宁,大有玄机啊!”
王继文问:“阚公以为有何玄机?”
阚祯兆道:“只怕西北有战事了。”
王继文说:“我也是这么猜想的,但朝廷只让我们解粮饷,别的就不管了。阚公,您看这个地方行吗?”
阚祯兆抬眼望去,但见滇池空阔,浮光耀金,太华山壁立水天之际,其色如黛。阚祯兆道:“此处甚好,抚台大人,只怕再没这么好的地方了。”
王继文极目远眺,凝神片刻,不禁连声叫好。又吩咐风水先生摆开罗盘,作法如仪。从者亦连连附和,只道是形胜之地。大观楼址就这么定了。
真正叫人头痛的事是协饷。一日,王继文同阚祯兆、杨文启商议协饷之事,问道:“阚公,库银还有多少?”
阚祯兆说:“库银尚有一百三十万两。”
杨文启很是担忧,说:“抚台大人,今后没了铜税,真不知哪里弄银子去。”
阚祯兆道:“只有开辟新的财源了。”
王继文叹道:“谈何容易!”
阚祯兆说:“我同犬子望达琢磨了一个税赋新法,现在只是个草案。改日送抚台大人过目。”
王继文听了并不太在意,只道:“多谢阚公操心了。我们先商量协饷吧,朝廷都催好几次了。我云南每次协饷,都是如期如数,不拖不欠,皇上屡次嘉赏。这回,我们也不能落在别人后面!”
阚祯兆说:“要在短期内筹足十七万两饷银,十三万担粮食,一万匹军马,非同小可啊!抚台大人,以我之见,不如向朝廷上个折子,说说难处,能免就免,能缓就缓。”
王继文摇头道:“不,我从随军削藩之日起,就负责督办粮饷,从未误过事。不是我夸海口,我王某办事干练,早已名声在外,朝野尽知。”
杨文启奉承道:“是啊,皇上很器重抚台大人的才干。”
阚祯兆说:“抚台大人,我真是没法着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