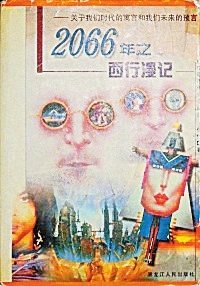西川的诗_西川-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共同的饥饿使他们拥抱,但是共同的语言他们宁肯不说。
走过歌剧院,走过洗衣店,像两名暗探他们混进别人的晚宴,在地下异乡他们找不到厕所。
三名警察将他们逮捕,十八名妇女控告他们龌龊。
他眼看昔日的债主出示伪造的通行证,而他只能掏出一小盒清凉油。
“请收下这微薄的礼物,”他说。但是牢房已经备好。他被蒙上眼睛推进牢房,他大喊大叫我是某某。
等他摘下眼罩他却怒气全消:他站在故乡的阳光大道。
c〇〇〇二四
有一朵荷花在天空漂浮,有一滴鸟粪被大地接住,有一只拳头穿进他的耳孔,在阳光大道他就将透明。
天空的大火业已熄灭,地上的尘土是多少条性命?他听见他的乳名被呼喊,一个孩子一直走进他的心中。
他心中的黎明城寨里只有一 把椅子,他心中的血腥战场上摆开了棋局,他经历九次屈从、十次反抗、三次被杀、四次杀人。
月光撒落在污秽的河面,露水洗干净浪漫的鬼魂。
在狂欢节上,鬼魂踩掉他的鞋跟。厄运开始:他被浓眉大眼的家伙推出队列。
多年以后他擦亮第一根火柴。
“就这样吧,”他对一只蝴蝶小声耳语。
在蝴蝶清扫的道路两旁,在曾经是田埂的道路两旁,每一个院落都好象他当年背叛的家庭,每一只喜鹊都在堕落。
旧世界被拆除到他的脚边,他感觉自身开始透明。
忧伤涌上他的太阳穴,就像北斗七星涌上屋顶……一阵咳嗽,一阵头晕,让他把人生的台词忘得一干二净。
d〇〇〇五九
他曾经是楚霸王,一把火烧掉阿房宫。
他曾经是黑旋风,撕烂朝廷的招安令。
而现在他坐在酒瓶和鸟笼之间,内心接近地主的晚年。他的儿子们长着农业的面孔,他的孙子们唱着流行歌曲去乡村旅行。
经过黑夜、雾霭、雷鸣电闪,他的大脑进了水。他在不同的房间里说同样的话,他最后的领地仅限于家庭。
他曾经是李后主,用诗歌平衡他亡国的罪名。
他曾经是宋徽宗,允许孔雀进入他的大客厅。
但他无力述说他的过去:那歉收、那丰收、那乞丐中的道义、那赌徒中的传说。他无力述说他的过去,一到春天就开始打嗝。
无数个傍晚他酒气熏天穿街过巷。他漫骂自己,别人以为他在漫骂这时代的天堂。他贫苦的父亲、羞惭的父亲等在死胡同里,准备迎面给他一记耳光。
他曾经是儿子,现在是父亲;他曾经是父亲,现在玩着一对老核桃。
充满错别字的一生像一部无法发表的回忆录;他心中有大片空白像白色恐怖需要胡编乱造来填补。
当他笼中的小鸟进入梦乡,他学着鸟叫把它们叫醒。他最后一次拎着空酒瓶走出家门,却忘了把钥匙带上。
e〇〇一八三
子曰:“三十而立。”
三十岁,他被医生宣判没有生育能力。这预示着他庞大的家族不能再延续。他砸烂瓷器,他烧毁书籍,他抱头痛哭,然后睡去。
子曰:“四十而不惑。”
四十岁,笙歌震得他浑身发抖,强烈的犯罪感使他把祖传的金佛交还给人民。他迁出豪宅,洗心革面:软弱的人多么渴求安宁。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五十岁的妻子浑身粥渍。从他任教的小学校归来,他给妻子带回了瓜子菜、回回菜和一尾小黄鱼。迟到的爱情像铁锅里的油腥。
子曰:“六十而耳顺。”
而他彻底失聪在他耳顺的年头:一个闹哄哄的世界只剩下奇怪的表情。他长时间呆望窗外,好象有人将不远万里来将他造访,来喝他的茶,来和他一起呆望窗外。
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在发霉的房间里,他七十岁的心灵爱上了写诗。最后一颗牙齿提醒他疼痛的感觉。最后两滴泪水流进他的嘴里。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孔子死时七十有三,而他活到了死不了的年龄。
他铺纸,研墨,蘸好毛笔。但他每一次企图赞美生活都时白费力气。
f〇〇二〇二(身份不明)
别人的笑声:别人在他的房间里。他脑海中闪现第一个词:勾当!他脑海中闪现第二个词:罪行!
他用力推门,但门推不开。他拼命高喊:“滚出去!”但他分明是在乞求:他唱过太多的靡靡之音。
进不了自家的门,好象进不了说话的收音机:好象每一件事物都在播音,他甚至听到肚子里有人在行酒令。
来了满街的裁缝,来了满街的保姆,他们劝他“忍着点儿”。
但他硬是把手指抠进喉咙,命令肚里的家伙:“滚出去!”
一阵呕吐让他清爽,一只死耗子让他绕行。他追上快乐的人群,进入百花盛开的园圃。他听到众人喝斥:“滚出去!”
(哦,谁能代替他滚出去,他就代替谁去死。)
天空飘满别人的云朵,他脸上挂着别人的石灰。城门洞里牧羊人吃光了自己的羊群,他递上手绢让他擦嘴。
他再次回到自家的门口,听见房间里的笑声依旧不息。他再次高喊:“滚出去!”回答他的也是“滚出去!”
“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这声音重复三遍以后听起来就像一首诗。
h〇〇〇三二五
生为半个读书人的他依赖于既定的社会秩序,而他的灵魂不同意。
他若突然死亡,一群人中间就会混乱迭出。而对此他的灵魂恰好充满好奇。
在一群人中间他说了算,而他的灵魂了解他的懦弱。
他在苹果上咬出行政的牙印,他在文件上签署蚯蚓的连笔字,而他的灵魂对于游戏更关心。
在利益的大厦里他闭门不出,他的灵魂急躁得来回打转。
水管里流出的小美人儿让他发愣,太美的人儿使他阳痿,而他的灵魂扑上去。
他必须小心掩饰自己的心跳,他的敌人要将他彻底揭穿,而在两者的灵魂之间建立起友谊。
他从权衡利弊中学会了抒情,他率领众人歌颂美好的明天,而他的灵魂只想回到往昔,
回到夜晚九点的江上扁舟,回到清晨六点的山中小径,而他不能这样做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毁了他一个下午的好心情。他放下电话,眺望日落处绵亘的群山,一群他猛然想到的野兽惊得他冒出一身冷汗,而他得灵魂正在长出锋利的犬齿。
j〇〇五六八(身份不明)
一个纸人,在墨水里泡蓝。
一个纸人,在晨光中眩晕。
他有了影子,有了名字,决心大干一场。他学会了弯腰和打哈欠。
他寻找灵魂出窍的感觉:“那也许就像纸片在空中飞落。”
他好奇地点燃一堆火,一下子烧掉一只胳膊。
他必须善于自我保护,他必须用另一只手将命运把握。
教条和习俗拦住他,懒散的人群要将他挤瘪。他试着挥起先知的皮鞭,时代就把屁股撅到他面前。
在第一个姑娘向他献花之后他擦亮皮鞋。但是每天夜里,衬衫摩擦出的静电火花都叫他慌乱。
他慌乱地躲进书页,他慌乱地掉进纸篓;他在纸篓中高谈阔论,他把慌乱转变为挑战。
挑战那些血肉之躯,用纸张糊一把纸人的安乐椅。
他模仿人类的声音,他模仿人类的雄心。
如果你用针来刺他的手指,他不会流血;如果你打击他,实际上打击的却是别人。
k〇一七〇四
谦卑是唯一一种不能赢得爱情的美德。
忍耐最终把自己变成一幢无人居住的大厦。
比如这个人,把沉默闭在嘴里,避开政治的弄罚。数十个年头,在红色首都,为了爱一个女人他需要自由。
他看到无聊的女性在身边走动,而那伟大的女性引领别人上升。
伟大的女性如同幻影。他攀上幻影的楼梯,他犹豫再三去造访那幻影一家人,开门的小姑娘说:“你敲错了门。”
踯躅在两个家庭之间,四季的风景越来越平淡。只有风雨中淫荡的幻想越来越灿烂。一个孤独的公子哥荡起地狱里的秋千。
杯中的茶水凉了,旧相册不翼而飞。他的心脏发出怪声,他的梦境推向剧终。他死在妻子的身边:一具尸体那是我们的老孟。
他化作一个佝偻的幻影,至死没有交出爱情的黑匣子。
现在他已可以飘入那伟大女性的高楼上的窗口。这就是老一代的风流韵事,只有傻瓜才为之心痛。
l〇一九三三
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小个子男人走起路来一摇三摆。
这个后来死于抒情的小个子男人在办公室里插满鲜花。
早年不曾得到的东西他都要一一自我补偿;早年的屈辱成为他俗艳一生中最动人的篇章。
时代需要小聪明:觞光杯影,他躬逢其盛;而智慧何用;智慧只适用于那些荒山秃岭。
他穿梭在要人和女人之间,他浪漫的鼻头微微发红。他唯一的仇人是他的妻子,老式婚姻妨碍他的前程。
他打好领带,喷好香水,等待着,盘算着,要在天安门广场的十万人舞会上独占衣衫单薄的舞会皇后。
夏日炎炎,夜晚闪烁流星。他打死一只蚊子,飞来另一只蚊子;一个男人来到他面前,向他宣布组织的决定。
好运走到了头。四十岁,他看到了死亡。组织明察秋毫:他刚刚猥亵的女人相貌平庸。
他爬上百米高的烟囱以消散胸中的郁闷,险些化作一阵浓烟飞上苍天。他向苍天发誓绝不自我否定。
但最终在一次飞行中被苍天所否定。
n〇五一八〇(身份不明)
小的是美的,小的是干净的,小的是安全的。
像鸡蛋一样小,像纽扣一样小,更小,更小,最好像昆虫一样厝身于透明的琥珀里。
毛巾上滞留着他的汗渍,草叶上滞留着他的脚印。他并非不能制造垃圾,只是不想让自己成为垃圾;他通过缩小自己来达到目的。
尘土扑了他一满脸,他缩小一下。
走在路上,想起一个笑话,他哈哈大笔,他缩小一下。
孩子们用放大镜聚集太阳的光芒,他一闪身躲过那滚烫的焦点。但他的身上还是冒起了青烟。
他已不辨方向,他已不辨物体。他爬上火车的额头,幸好那冒失鬼一动未动。
世界之大全在于他身子之小。他愈贴近大地,便愈害怕天空。
他冒险抓住生锈的弹簧,他心满意足地在落叶下躲雨。
没有朋友,没有敌人,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孤独的蛋糕。
没有任何禁区他不能进入,没有任何秘密他不能分享。但太小的他甚至无法爱上一个姑娘,甚至无法惹出最小的麻烦。
o〇九七三四
他出生的省份遍布纵横的河道、碧绿的稻田。农业之风吹凉了他的屁股。他请求庙里的神仙对他多加照看。
他努力学习,学习到半夜女鬼为他洗脚;他努力劳动,劳动到地里不再有收成。
长庚星闪耀在天边,他的顺风船开到了长庚星下面。带着私奔的快感他敲开尼禄的家门,但漫步在雄伟的广场,他的口臭让尼禄感到厌烦。
另一个半球的神祗听见他的蠢话,另一个半球的蠢人招待他面包渣。
可在故乡人看来他已经成功:一回到祖国他就在有限的范围里实行起小小的暴政。
他给一个个抽屉上了锁。
他在嘴里含着一口有毒的血。
他想象所有的姑娘顺从他的蹂躏。
他把一张支票签发给黑夜。
转折的时代,小人们酒足饭饱。他松开皮带,以小恩小惠换得喝彩。
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他横尸于他的乡间别墅,有人说是谋杀,有人说是自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