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水北_韩少功-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扑进画框
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
汽车爬高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车头大喘一声,突然一落。一片巨大的蓝色冷不防冒出来,使乘客们的心境顿时空阔和清凉。前面还在修路,汽车停在大坝上,不能再往前走了。乘客如果还要前行,投访蓝色水面那一边的迷蒙之处,就只能收拾自己的行李,疲惫地去水边找船。这使我想起了古典小说里的场面:好汉们穷途末路来到水边,幸有酒保前来接头,一支响箭向湖中,芦苇泊里便有造反者的快船闪出……
这支从古代射来的响箭,射穿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新中国,疾风嗖嗖又余音袅袅——我今天也在这里落草?
我从没见过这个水库——它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是我离开了这里之后。据说它与另外两个大水库相邻和相接,构成梯级的品字形,是红色时代留下的一大批水利工程之一,至今让山外数十万亩农田受益,也给老山里的人带来了驾船与打鱼一类新的生计。这让我多少有些好奇。我熟悉水库出现以前的老山。作为那时的知青,我常常带着一袋米和一根扁担,步行数十公里,来这里寻购竹木,一路上被长蛇、野猪粪以及豹子的叫声吓得心惊胆颤。为了对付国家的禁伐,躲避当地林木站的拦阻,当时的我们贼一样昼息夜行,十多个汉子结成一伙,随时准备闯关甚至打架。有时候谁掉了队,找不到路了,在月光里恐慌地呼叫,就会叫出远村里此起彼伏的狗吠。
当时这里也有知青点,其中大部分是我中学的同学,曾给我提供过红薯和糍粑,用竹筒一次次为我吹燃火塘里的火苗。他们落户的地点,如今已被大水淹没,一片碧波浩渺中无处可寻。当机动木船突突突犁开碧浪,我没有参与本地船客们的说笑,只是默默地观察和测量着水面。我知道,就在此刻,就在脚下,在船下暗无天日的水深之处,有我熟悉的石阶和墙垣正在飘移,有我熟悉的灶台和门槛已经残腐,正在被鱼虾探访。某一块石板上可能还留有我当年的刻痕:一个不成形的棋盘。
米狗子,骨架子,虱婆子,小猪,高丽……这些读者所陌生的绰号不用我记忆就能脱口而出。他们是我知青时代的朋友,是深深水底的一只只故事,足以让我思绪暗涌。三十年前飞鸟各投林,弹指之间已不觉老之将至——他们此刻的睡梦里是否正有一线突突突的声音飘过?
巴童浑不寝,夜半有行舟。这是杜甫的诗。独行潭底影,数息身边树。这是贾长江的诗。云间迷树影,雾里失峰形。这是王勃的诗。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孟浩然的诗。芦荻荒寒野水平,四周唧唧夜虫声。这是《阅微草堂笔记》中俞君祺的诗。……机船剪破一匹匹水中的山林倒影,绕过一个个湖心荒岛,进入了老山一道越来越窄的皱折,沉落在两山间一道越来越窄的天空之下。我感觉到这船不光是在空间里航行,而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画廊里巡游,驶入古人幽深的诗境。
我用手机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在柴油机的轰闹中听不太清楚,只听到他一句惊讶:“你在哪里?你真地去了八溪?”——他是说这个乡的名字。
为什么不?
“你就打算住在那里?”
不行吗?
我觉得他的停顿有些奇怪。
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我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在城市。我的工作也离不开轰轰城市。但城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越来越陌生,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也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疯,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
“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酒吧里的男女们疲惫地追问,大多找不出答案。就像一台老式留声机出了故障,唱针永远停留在不断反复的这一句,无法再读取后续的声音。这些男女通常会在自己的墙头挂一些带框的风光照片或风光绘画,算是他们记忆童年和记忆大自然的三两存根,或者是对自己许诺美好未来的几张期票。未来迟迟无法兑现,也许永远无法兑现——他们是被什么力量久久困锁在画框之外?对于都市人来说,画框里的山山水水真是那样遥不可及?
我不相信,于是扑嗵一声扑进画框里来了。
地图上的微点
几年前我回到了故乡湖南,迁入乡下一个山村。这里是两县交界之地,地处东经约113。5度,北纬约29度。洞庭湖平原绵延到这里,突然遇到了高山的阻截。幕阜山、连云山、雾峰山等群山拔地而起,形成了湘东山地的北端门户。它们在航拍下如云海雾浪前的一道道陡岸,升起一片钢蓝色苍茫。
山脉从这里跃起,一直向南起伏和翻腾,拉抬出武功山脉和罗宵山脉,最终平息于遥不可及的粤北。我曾找来一本比一本比例尺更大的地图,像空降兵快速降低高度,呼呼呼把大地看得越来越清楚,但最终还是看不见我的村庄。我这才知道,村庄太小了,人更是没有位置和痕迹。那些平时看起来巨大无比的幸福或痛苦,记忆或者忘却,功业或者遗憾,一旦进入经度与纬度的坐标,一旦置于高空俯瞰的目光之下,就会在寂静的山河之间毫无踪迹——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
浩阔的地貌总是使人平静。
回到从前
我在地图的一个微点里存在过,当过六年的插队知青,至“文化革命”结束才进入另一些微点,比如大学和都市。我在更微点的大楼和更更微点的公寓和更更更微点的房间里突然两鬓生霜。
有人把我的村庄叫作“马桥”。其实“马桥”是我在某篇小说中一个虚构的地名,也是中国农村常见的地名,与我的去向没有特别关系。还有记者说过,我移居乡下是出于对文坛的失望——这是指我卷入了90年代一场思想冲突,不料招怨于一些论敌,受到媒体上谣言浪潮的狠狠报复。﹡其实,这位记者并不知道,早在风波发生之前,我已在山里号下了宅地,盖起了房子,与报复毫无关系。甚至早在80年代我进入城市不久,我妻子就在一篇文章里就透露:“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现在不说。”——那个秘密其实就是将来返乡的打算。
实在是蓄谋已久。
我生性好人少而不是人多,好静而不是好闹。即便是当知青的时候,除了贫困让人深深焦虑,大自然的广阔和清洁从不让我烦恼,并且在后来很多文学作品中一直是我心中的兴奋。进入城市以来,我梦得较多的场景之一就是火车站,是我一次次迟到误车,是我追着车尾的好一番焦急和狼狈——却不知道我为何要上这一趟车。我猜想这无非是一种提醒,是命运召唤我去一个未知之地。
我居住长沙或海口的时候,也总是选址在郊区,好像城市是巨大的旋涡,一次次把我甩到了边缘,只要高楼丛立的城市旋转得更快一点,只要我捏住钥匙串的手稍稍一松,我就会飞离一张张不再属于我的房门,在呼啦啦的风暴中腾空而去,被离心力扔向遥远的地方。
1971年的农历除夕,我决心逃离农村。深夜的炉火奄奄一息,几位从各地回城探亲的知青围炉聚首,久久地沉默无言,只有长吁短叹。一个胆大妄为的地下圈子,曾投入诗歌、哲学以及有关毛泽东的辩论,眼下已经情绪降温。不知是谁,仍以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宏论:去他妈的农村!我们都应该进城,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才是革命的火车头!
我们几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羞于抱怨农村的艰苦和青春的苦闷,却乐于夸张自己的历史责任。既然喂猪不好玩了,农民夜校不好玩了,小提琴与演出队也不好玩了,那么,“知识分子”四个字真是令人神往。我们不自量力地迅速决议:谁进入哲学,谁进入史学,谁进入外语,谁进入经济学……至于我,年龄最小,什么也不大懂,就捡了文学这个象征性和简易性的差事,如同在总攻击开始时跟着扔扔石头。
三十年过去了,回想起当年那个浪漫的除夕,回想起当时大家很搞笑的紧紧握手和暗语接头:“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朋友们早已从一部想象的激情政治电影中回到了平庸的现实生活。一语居然成谶:那一次除夕的聚会者,其大多数后来果然成了教授、画家或者作家,完成了地下团伙派定的任务。不过,时代已经大变,市场化潮流只是把知识速转换成利益,转换成好收入、大房子、日本汽车、美国绿卡,还有大家相忘于江湖后的日渐疏远,包括见面时的言不及义。
如果不是餐宴,有些人哈欠连连,甚至找不到见面的借口。“革命”在哪里?“消灭法西斯”和“自由属于人民”是否从来只是一句戏言?
又有一名老知青去世了,是失业以后无钱治病而夭折的。加上以前的两位,已有三名同伴离我而去。这是成功人士圈子以外的事情。更多的工人在失业,更多的农民在失地,更多的垃圾村和卖血村在高楼的影子里繁殖,这也是成功人士圈子以外的事情,而且从来不会中断圈子里的戏谑,甚至不能在宴会上造成哪怕一秒钟的面色沉重。但沉重又怎么样?脸色沉重以后就不再炒卖楼宅、不再收罗古玩、不再出国度假、不再对利益关系网络中所有重要人物小心逢迎了吗?不,生活还是这样,历史还是这样。及时的道德表情有利于心理护肤,但不会给世界增加或减少一点什么。
我感到心跳急促,突然有一种再次逃离的冲动——虽然这一次不再有人相约。我也许该走远一点,重新走到上一次逃离的起点,去看看我以前匆忙告别的地方,看看记忆中一个亮着灯光的窗口,或是烈日下挑担歇脚时一片树荫——是不是事情从那里开始错起?人生已经过了中场,留下大堆无可删改的履历,但我是不是还异想天开地要操着橡皮擦子从头再来?
一个葡萄园里的法国老太婆曾向我嘟哝:“接近自然就是接近上帝。”问题是:我相信上帝吗?相信那个从来只会转移苦难但从来不会消除苦难的上帝吗?相信那个从来只会变换不公但从来不会取消不公的上帝吗?相信那数十个世纪以来一直推动我们逃离但从不让我们知道理由所在和方向所在的上帝吗?
我喜爱远方,喜欢天空和土地,只是一些个人的偏好。我讨厌太多所谓上等人的没心没肺或多愁善感,受不了颇繁交往中越来越常见的无话可说,也只是一些个人的怪癖。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连自己有时也不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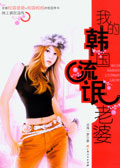
![[韩治国] 忆秦娥封面](http://www.beike3.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