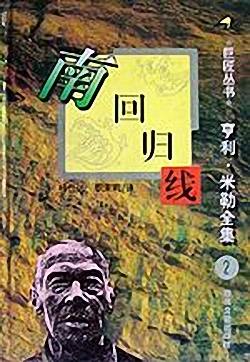北回归线-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晴,下冰雹、雨夹雪、雪、打雷、闪电、战争、饥馑、瘟疫,都不受丝毫影响。总
是同样的恼人温度,同样的胡言乱语,同样的在脚腕上系带子的鞋和上帝的小安滇
儿唱男高音和女高音。靠近出口处有一只开了一个孔的小箱子,是为了继续天国的
工作的,于是上帝的恩典便会像雨点一样落在帝王头上,落在国家里,落在军舰、
高效炸药、坦克和飞机上,于是工人会增强臂力,有力气屠宰马、牛和羊,有力气
在铁大梁上钻孔,有力气在别人的裤子上缀扣子,有力气出售胡萝卜、缝纫机和汽
车,有力气消灭虫子、打扫马棚、倒垃圾箱、洗刷厕所,有力气写新闻标题、在地
下铁道里剪票。力气……力气,原来这喃喃自语和戏弄人的把戏只是为了给人一点
力气。
们突然来到了一个小广场,那便是圣克洛蒂尔德教堂,人们正在望弥撒。菲尔
莫的头还有一点儿昏昏沉沉,他执拗地也要去望弥散,据说是“为了好玩”。我对
此有几分不安,首先是因为我从未望过一次弥撒,其次是我显得寒酸,也觉得寒酸
。菲尔莫也显得衣衫褴搂,甚至比我还不体面,他歪戴着大垂边帽,大衣上还沾着
我们刚去过的最后一家妓院里的锯末。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大踏步走进去了,最糟
的不过是被他们推出来而已。
看到的景象令我吃了一惊,也就一点儿忐忑不安的感觉也没有了。过了一会儿
我才习惯了昏暗的光线,我牵着菲尔莫的袖子,跟在他身后踉踉跄跄地走,这时一
种稀奇古怪的声音钻进了我的耳朵,像某种从铺路的冷石板中冒出的空洞的嗡嗡声
。
这是一座巨大的、凄凉的坟墓,来吊丧的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是到地下那
个世界去之前必经的来宾接待室,温度在华氏五十五或六十度左右,没有音乐——
除了地窖最上层放出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哀乐,活像百万棵菜花在黑暗中哀号。身着
寿衣的人口中念念有词,一副无可奈何、十分沮丧的乞丐模样,这些乞丐恍恍惚惚
地伸出手来,咕哝着谁也听不懂的乞求怜悯的话。
我早知道会有这类事,不过一个人若还知道有屠宰尝停尸所和解剖室这类去处
,他会出于本能地躲开这些地方。我在街上常常从一个牧师身边走过,他手里捧着
一本小小的祈祷书在吃力地背诵。“傻瓜!”我自语道,过后也就不去理会了。在
街上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呆子,这个牧师还不算是最叫人吃惊的。
人类两千年的蠢行已使我们对此不那么敏感了,然而当你被突然送到这个牧师
身边,看到他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发挥着一座闹钟的作用,你还是会产生一些全然
不同的情感的。
一刹那间全部这些流涎水、翁动嘴唇的把戏几乎都有了意我们从一个地方挪到
另一个地方,以通宵狂欢后的那种清醒意识审视这个场面。我们这样穿来穿去一定
很惹人注意,因为我们的外衣领子竖着,从不画十字,除了低声说几句麻木不仁的
话以外嘴巴一动也不曾动。若是菲尔莫不那么固执地要在仪式正进行了一半的时候
从祭坛边走过,或许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一切。他在找出口,我估计他想到了出口那
儿就好好看一看这最最神圣的场面,这就是说要近距离仔细看一看。我们一直平安
无事,正在朝很可能是出去的通道那一道光线处走去,这时幽暗中猛地闪出一位牧
师拦住了路。他想问问我们要去哪儿,正在于什么,我们相当有礼貌地回答说我们
正在找出口。我们说的是英语的“出口”,因为当时太惊恐,我们一时想不起法语
“出口”是怎么说的了。牧师一句话不说便紧紧抓住我们的胳膊,推开一道边门把
我们狠狠推出去了,我们摇摇晃晃地跌进了刺眼的阳光中。这件事发生得那么突然
、猝不及防,待我们到了人行道上仍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我们眯上眼睛走出去几步
,然后又出于本能转过身来。牧师仍站在台阶上,苍白得像一个鬼魂,像魔鬼那样
狠狠地瞪着我们,准是连肺都气炸了。后来又回想起这件事时我也不怪他,不过当
时瞧见他穿着长袍、头上扣着一顶小瓜皮帽的滑稽相,我禁不住哈哈大笑。我看看
菲尔莫,于是他也大笑开了。我们站在那儿当着这个可怜虫的面足足笑了一分钟,
我猜他起初有一点儿茫然不知所措,不过他突然冲下台阶,一边还冲着我们晃拳头
,像是认真了。待他冲出围墙便狂奔过来,这会儿某种保护自乙的本能提醒我快溜
走。我拽住菲尔莫的袖子跑开了,他还像个傻瓜似的说,“别,别!我不跑!”“
快跑!”我嚷道。“咱们还是快点儿离开这儿为妙,这家伙已经完全疯了。”于是
我们逃了,拼命竭尽全力逃走了。
去第戎的路上我们仍在为这件事情大笑,不过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另一件可笑的
往事上。那件事同今天发生的事有点儿相似,是我在佛罗里达短暂停留时发生的。
那是在出名的繁华时期,我同成千上万人一样冷不防遇到了麻烦,我试图解脱,结
果却同一位朋友一道更深地陷入了困境。杰克逊维尔尤其处于被围困状态中,我们
就在那儿被困了大约六个星期。天下所有的流浪汉和许多以前从未作过流浪汉的家
伙似乎都游荡到杰克逊维尔来了,到处都住满了人——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消
防队和警察局、旅馆和公寓。到处都挂着客满的牌子,绝对客满。杰克逊维尔的居
民的心肠已经变得很硬,我觉得他们像是穿着甲胄在来回走。这一回又是食物这个
老问题,食物和一个睡觉的地方。食物正从南方用火车运来。桔子、柚子以及各种
水份很多的食品。我们常从货车棚旁走过,看看有没有烂水果,可甚至连这也很难
得。
在绝望中,有一天夜里我拉上我的朋友乔来到一家犹太教会堂里,当时里面正
在做礼拜。这是一家新派会众聚会场所。那位拉比给我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音乐
也很打动人,是犹太人那种发自内心的悲哀曲调。礼拜刚一结束我便大摇大摆地走
到拉比的书房里要求见他,他接待我时还算过得去,待我说明了来意他便吓坏了。
我只是求他给我和我的朋友乔施舍几个钱,可是看着他瞧着我的那副样子你还以为
我已开口要把会堂租下来当保龄球场呢。最后他突然直截了当地间我是不是犹太人
,我说不是,他便发火了。那么,请问,你为什么要来向一个犹太教牧师求援呢?
我天真地告诉他我一贯信任犹太人,我是很谦卑他说这话的,仿佛自己不是犹太人
是一个古怪的缺陷似的。这也是实话,但他根本不为所动。不,先生。他简直吓坏
了。为了赶我走,他给救世军的人写了一张便条,说,“这才是你该去的地方呢。
”说完他便无礼地转身照看他的会众去了。
救世军当然也拿不出什么给我们。假如我们每人有两毛五分也可以祖一个铺在
地上的床垫,可是我们两人加起来连五分钱也没有。我们来到公园里,在一条长椅
上躺下。天正在下雨,我们便用报纸遮盖在身上。估计过了还不到半小时,一个警
察过来一句话不说就狠狠扇了我们一掌,我们马上爬起来站在地上,还跳了几下舞
,尽管当时没有一点儿心思跳舞。屁股上挨了那白痴王八蛋掴了一掌后,我真是又
气愤又可怜,又沮丧又下贱,简直恨不得把市政厅炸掉。
第二天早上,为了报复这伙好客的王八蛋,我们一早便精神焕发地站在一个天
主教教士的门口了。这一回我让乔说话,他是爱尔兰人,还带点儿爱尔兰土腔。他
的眼睛也非常蓝,温情脉脉的,只要乐意他还能叫它们湿润起来。一个穿黑袍的修
女打开门,可她并不请我们进去,却要我们在走廊里等她去禀报那位好心的长老。
过了几分钟那位好心的长老来了,像一部火车头一样喘着粗气。我们这么早打搅他
的嗜好是为了得到什么?
一点儿吃的和一个睡觉的地方,我们天真地答道。好心的长老立即问,那你们
是从哪儿来的?从纽约。从纽约吗?那么你们还是尽快回纽约去吧,我的孩子们。
这个大块头、大胖萝卜脸的狗东西再也没有说什么便当着我们的面把门关上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俩像两只歪歪倒倒的双桅帆船一样无助地四处乱逛,又
碰巧从教士家路过。老天爷在上,这个大块头、淫荡的萝卜脸正在从胡同里往外倒
他的轿车呢!从我们身边疾驶而过时他朝我们眼睛里喷出一团烟,似乎是说,“这
是赏给你们的!”那轿车很漂亮,后面装着好几只备用轮胎,好心的长老坐在方向
盘后面,嘴里叼着一根粗雪茄。这根雪茄这么粗,味道这么足,准是一根克罗那·
克罗那牌的。他坐姿很优雅,你很难模仿得来。我看不见他是否穿了长袍,只看到
嘴边淌下的肉汤和那根散发出香味的五十美分大雪茄。
去第戎的路上我不由得追忆起这段往事。我想到在那些痛苦、耻辱的时刻我本
该说、本该做而又没有说、没有做的一切,那时为了向别人讨一口面包就要叫自己
变得不如一条虫子。尽管我非常镇定自若,这些老一套的侮辱和伤害仍使我感到痛
苦。
我仍能感觉到那个警察在公园里朝我屁股上掴的那一巴掌,尽管那只是一桩小
事,你或许会说那是一堂短短的舞蹈课。我走遍了整个美国,也曾进入加拿大和墨
西哥。到处都一样,你若想要面包就得去干活,去受人摆布。整个地球是一片灰蒙
蒙的沙漠,是钢和水泥铺成的地毯。生产吧!更多的傻瓜和螺钉、更多的带刺铁丝
网、更多的狗食、更多的割草机、更多的滚珠轴承、更多的高效炸药,更多的坦克
、更多的毒气、更多的肥皂、更多的牙膏、更多的报纸、更多的教育、更多的教堂
、更多的图书馆、更多的博物馆。前进!时间不等人,胎儿正在穿过子宫颈,却连
一点润滑通道的羊水也没有。这是干燥、快把胎儿勒死的出生,没有一声哭号、一
声喊叫。向来到人世间的孩子致敬!从直肠里腾腾放出二十一响致敬的礼炮。瓦尔
特·惠特曼说,“我戴帽子全看自己高兴不高兴,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以
前有过你可以挑选一顶合适的帽子戴的时代,不过时代在变,现在为了挑选一顶合
适的帽子你得一直走到电椅上去,他们会给你一顶瓜皮帽戴。有点紧,怎么啦?不
过没关系!挺合适。
你必须呆在法国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在将生与死分为两部分的子午线上行
走,这样才会明白前面等待你的将是何种难以预测的景观。带电的肉体!民主的灵
魂!血的浪潮!上帝的神圣母亲啊,这一番蠢活是什么意思?地球烤焦了,破裂了
,男男女女像一窝兀鹰围着一具发臭的尸体一样汇集在一起,交配,然后飞往各处
。我门就是从云里像沉重的石头一样落下的兀鹰,就是它们的爪和嘴,它的巨大的
消化器官有一个专嗅臭肉的鼻子。前进!不怜悯、不同情、不爱也不谅解地前进!
别请求宽恕,也别宽恕别人!更多的战舰、毒气、高效炸药!更多的淋菌!更多的
链球菌!更多的轰炸机!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