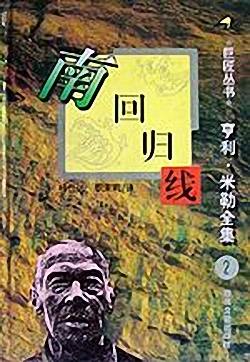北回归线-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乐就像在死牢里做梦喝香槟一样荒唐,音乐是我最不在意的东西。我甚至连女人也
不想了,因为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沮丧、寒冷、荒芜、阴暗。头一天晚上回家时我注
意到一家咖啡馆的门上刻着高康大的话。咖啡馆内部却像一个停尸所。不管怎样,
还是往前走吧!
我有的是时间,却没有一文钱花。我一天只上两三个小时的会话课,以后就没
有事了。教这些可怜虫英语又有什么用呢?
我真替他们难过,整个上午苦苦地念《约翰·吉尔平的旅行》,到了下午又上
我这儿来练习一种死去的语言。我想起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读维吉尔的作品或是吃
力地念《赫尔曼和多罗特哑》这类谁也看不懂的废话。真是疯了!学问是只空面包
篮!
我又想起卡尔,他能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他每写一本书都要在里面拼命恭
维不朽的、千古流芳的歌德。尽管如此,卡尔却缺乏常识,找不到一个阔女人,无
法弄一身换洗内衣。这种以排队领救济食品和住防空洞告终的、对过去的眷恋中有
一种讨人厌的感伤,这种精神上的喧哗是令人讨厌的,它竟许可一个白痴往德国大
炮、无畏战舰和高效炸药上洒圣水。每一个满腹经纶的人都是人类的敌人。
我来到了这儿,本是来传播法美友好福音的。我是一具僵尸的使者,他四处掠
夺,酿成难以描述的痛苦和不幸,现在却梦想要建立世界和平了。呸!我真不明白
,他们指望我讲什么?
讲《草叶集》、讲关税壁垒、讲美国的《独立宣言》、讲最近一次流氓团伙之
间的火并?讲什么?我想知道要我讲什么。唉,告诉你们,我从未提起这些。我开
门见山,讲了一堂爱情生理学。
我讲的是:大象怎样做爱。这一招灵极了,第一天过后便再也没有空板凳了,
头一堂英语课后他们都站在门口等我到来。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们提各种问题,像
是屁也没学会一样。我让他们不停地问,我教他们提出更难以启齿的问题。“什么
都尽可以问。”——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在这儿我像一个来自无拘无束的精灵的国
度里的全权大使,来这儿旨在创造狂热和激动的气氛。一位著名天文学家说,“在
某些方面,物质世界像一个讲过的故事一样悄然逝去,像幻觉一样化为乌有。”看
来这话表达了在学问的空面包篮后面大家的普遍看法,我自己却不信这话,我不信
这伙王八蛋企图硬往我们肚子里塞的一切鬼话。
如果没有书可看,不上课时我就上楼到学监的宿舍里找他们闲聊。他们对周围
发生的一切无知得可笑,尤其对于艺术界的事情,他们差不多同学生一样无知。我
好像闯进了一所没有标明出口的、私人开办的小疯人院一样,有时我在拱廊下窥探
,看着孩子们大步走过去,脏兮兮的缸子里插着大块大块的面包。
我自己总是觉得饥饿难忍,因为我根本不可能赶上早饭。早饭总在早晨一个荒
唐的时辰开,而那会儿睡在床上真是舒服极了。
早餐是大碗大碗的发蓝的咖啡和一块块白面包,没有奶油可抹。
午饭是菜豆或扁豆,撒进去一点点肉屑使它看起来开胃些。这种食物只适合给
做苦工的囚犯吃、给砸石头的囚犯吃。酒也很糟糕,不是搀了水就是变了味。这些
食物有热量,不过烹调不得法。据众人说,莱克诺姆先生应对此负责。这话我也不
信,人家花钱雇他,目的是要他不叫我们饿死就行。他并不问我们是否有痔疮或疗
疮,并不关心我们是嘴细还是嘴粗。为什么要关心?他只是受雇去用这么多克的菜
肴生产这么多千瓦的能量,一切都是以马力来计算的。这全在脸色青白的办事员早
晨、中午和晚上抄抄写写的厚帐本上仔细计算过,借、贷这两部分用一道红线从中
间隔开。
空着肚子在四合院里徘徊时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有一点儿痴狂,我有一
点儿像“愚蠢的查理”那个可怜虫,只是没有奥代特·德·尚帕狄丰来跟我玩牌。
有一半的日子里我得向学生讨烟抽,有时正上着课我就跟他们一起啃开了一点干儿
面包。炉子总灭,所以我很快便用完了配给的木柴。要哄得管宿舍的办事员拿出一
点儿木柴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最后我对此恼火极了,便上街去捡柴,像一个阿拉
伯人似的。我很惊奇,在第戎的街道上几乎捡不到能生火的柴。不过这些小小的征
集木柴的远证将我带到了陌生的地域,我渐渐熟悉了据信是以一位名叫菲利贝尔·
帕尔隆的已故音乐家命名的一条小街,那儿有好几家妓院。这块地方总是会叫人更
快活一些,有做饭的味道、有晾出来的衣物。我偶尔也看到在妓院里闲荡的可怜的
傻瓜,他们比在城镇中心见到的穷鬼还好一些,每次穿过一家百货店时我都会碰到
这些穷鬼。为了取暖我常常这样穿来穿去,我估计他们也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这样
做的。他们在寻找一个愿为他们买一杯咖啡的人,由于寒冷和孤独他们显得有一点
儿痴呆,而当蓝色的夜幕降临时整个城市都显得有几分痴呆。你可以任选一个星期
四在主要马路上散步,一直走下去也永远不会碰到一个胸襟宽大的人。六七万人—
—也许更多——穿着羊毛内衣,无处可去,无事可做。他们生产出一车车芥末。女
子管弦乐队笨拙地奏出《快乐的寡妇》。大旅馆里提供银质服务。一座公爵的宫殿
正在一块块、一点点地朽掉。树木在霜冻下发出尖厉的响声。木头鞋子不停地格登
格登响。那所大学在纪念歌德的忌日,或者是诞辰日,我记不清到底是哪一个了(
通常人们是纪念忌日的),总之这是一件蠢事,人人都在打哈欠、伸胳膊。
从马路上一路走进四合院,我总会产生一种深切的徒劳无功的感觉。院外是一
片凄凉和空虚,院里也是一片凄凉和空虚。
这座城镇笼罩在一种卑下的贫乏和啃书本的浓雾中,学的全是以往的渣滓。教
室分布在里院四周,很像在北方森林中见到的小屋,学究们就在这儿尽情大发宏论
。黑板上写着毫无用处的胡言乱语,法兰西共和国的未来公民得花毕生时间才能忘
掉这些胡话。有时在马路边的大接待室里接待家长们,那儿摆着古代英雄的半身塑
像,诸如莫里哀、拉辛、柯奈、伏尔泰之流。无论何时又一个不朽的人被摆进蜡像
馆后,内阁部长们总要用湿润的嘴唇提到所有这些稻草人(没有维荣的,拉伯雷的
和兰波的胸像)。总之,家长们和这些衬衣里塞了东西的蜡像在这庄严肃穆的会议
上碰到一起了。国家雇了这些蜡像来矫正年轻人的思想,总是这样矫正,总是用这
种美化庭院的方法使思想变得更有吸引力。小孩子们偶尔也上这儿来,人们很快便
会把这些小向日葵从托儿所里移植出去装饰城市的草坪。有些只是橡皮植物,只消
用一件破衬衣就可以很便当地掸去上面的尘土,一到晚上他们便急急忙忙没命地逃
进宿舍里去了。宿舍!
这儿亮着红灯,铃像消防队的警报一样呼啸,这儿的楼梯踏板由于人们常一窝
蜂涌向教室被踩出了空洞。
还有那些教师,起初几天我甚至同他们中的几个人握了手,当然在拱廊下擦身
而过时也总少不了碰碰帽子相互致意。可是根本谈不到倾心交谈,也谈不到走到街
角那儿一起喝上一杯。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有许多人显得像是吓破了胆。总
之我是属于另一阶层的,他们甚至不愿同我这种人分享一只虱子。只要一看到他们
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所以一看到他们过来我就暗暗诅咒。我常常靠着一恨柱子站在
那儿,嘴角上叼着一根烟,帽子扣在眼睛上,待他们走到听得见的地方我便狠狠啐
一口唾沫,再抬起帽子来。我甚至懒得张口同他们打招呼,我只是从牙缝里迸出一
句,“去你妈的,杰克!”说完就拉倒。
在这儿呆了一星期后我就觉得已在这儿呆了一辈子,这就像一场可怕的恶梦,
简直摆脱不了它。想着它我常常会昏睡过去。几天前我才到了这儿,当时夜幕刚降
下,人们在朦胧的灯光下像老鼠一样匆匆赶回家去,树木带着宝石尖般的恶意闪闪
发光,我不止一千次地想起了这一切。从火车站到这所学校一路上犹如穿越但泽走
廊的一次散步,到处毛茸茸的、有裂缝,令人神经紧张。这是死人尸骨铺砌的胡同
,下面埋着衣衫褴楼、歪七扭八、互相搂抱在一起的死人,还有沙丁鱼骨制成的脊
骨。
学校本身像是矗立在一层薄雪之上,它像一座倒置的山,其山顶直插地球中心
,上帝或魔鬼在那儿总穿着一件紧身衣干活,为那个始终不过是梦中遗精的天堂磨
面粉。如果太阳出来过我也不记得了,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从那边结了冰的
沼泽上吹过来寒冷、油腻的雾,铁道就是在那儿消失在阴郁的群山中去。距火车站
不远有一条人工运河,也许它是一条天然河也不得而知,它躲在黄色的天幕下,突
起的两岸边斜搭着一些小棚屋。我突然悟到周围还有一座兵营,因为我不时遇到一
些来自交趾支那的黄皮肤小个子,这伙扭来扭去、脸色焦黄的小矮个儿身着袋子似
的肥大军衣四处乱瞅,活像放在刨花中的干骨架。
这地方见鬼的中世纪遗风极难对付、极顽强,它低声呻吟着来回摇晃,从屋檐
下跳出来向你扑来,像被割断脖子的罪犯那样从滴水嘴上垂下来。我不断扭过头去
看身后,一直像一只挨脏叉子扎的螃蟹那样走路。所有这些肥胖的小怪物,所有粘
在圣米歇尔教堂正面墙上石板状的雕像都跟在我身后走过弯弯曲曲的小胡同、拐过
街角。圣米歇尔教堂的正面到了夜间便像一本集邮簿一样打开了,使你面对着印好
的纸张上的吓人景物。灯熄了,这些景物也从眼前消失,像文字一样静寂无声,这
时教堂正面的墙显得非常庄严雄伟。古老、粗糙的正面墙上的每一道缝里都回荡着
夜风的沉重呼啸声,冰冷、僵硬、呈花边状的碎石上洒了一层朦朦胧胧的、苦艾酒
般的雾和霜的涎水。
教堂耸立的这个地方的一切似乎都前后倒了个儿,教堂本身在几世纪以来雪的
侵蚀下也一定偏离了它的地基。它坐落在埃德加——基内广场,像一头死去的骡子
那样迎着风蹲着。风穿过莫奈街呼啸而来,像胡乱飘扬的白发。它绕着白色拴马桩
回旋,这些桩子挡住了公共汽车和二十匹骡子拉的马车的通道。有时清晨从这个出
口摇摇摆摆出来后我会同勒诺先生不期而遇,他像一个贪吃的修道士一样把自己裹
在修道士的长袍里,用十六世纪的语言同我攀谈。于是我同勒诺先生并排走,这时
月亮像被刺破的气球从油腻腻的天空中跃出,我亦立刻堕入了超然的王国中。勒诺
先生讲话干脆利落,像杏子一样淡而无味,带着很重的勃兰登保人的口音。他常常
一见到我就滔滔不绝地谈起歌德或费希特,深沉、凝重的声音在广场上顶风的角落
里发出隆隆的回声,像去年的雷鸣。尤卡坦人、桑给巴尔人、火地岛人,把我从这
张海绿色的猪皮下救出来吧!美国北部堆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