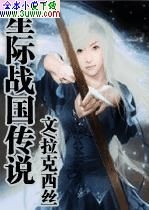蒋经国传-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7'蒋中正著《报国与思亲》,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陈布雷捉刀。
'8' 蒋中正著《哭母文》,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六月,收入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
'9'蒋锡候官至台州地方法院推事,“西安事变”时,积优成疾去世。
'10'同'3'。
'11' 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初版,台湾禁止公开出售。
'12' 《蒋总统秘录》:“蒋总统从留学的振武学校毕业,以‘士官候补生’身的,的发到驻屯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入伍,十二月五日报到。”高田即日本新泻县高田町,位北海道。第2册第210…212页(合北《中央日报》译本)。日文原名是《蒋介石秘史》,中文版删改之处甚多,已失本来面目。
'13'三月十八日,乃中国旧历惯例由王升、楚嵩秋、潘振球等为蒋设宴祝寿。
'14'《现代支那支录》,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
'15'同'11'。
'16'丁依著《蒋介石婚姻生活考》,原载香港《南北极》月刊。
2上海·北京·广州一九一六年,经国五岁,在家乡启蒙,纬国比他幸运,后来进的是县城培本幼稚园。
民国初年,中国的教育制度,止处在一个新旧交替.从旧式塾馆,过渡到新式学堂的蜕变阶段。但这就和把小脚放大那么困难,工作进展,非常缓慢:一方面死硬的保守派,永远抱残守缺:一方面经济的因素,师资、设备,都非一蹴可成、所以除了通都大邑,受西洋文化的冲击.开始创设了新式学堂。育人子弟的事.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和千百年前,一脉相承,操纵在腐酸的职业教书匠手里。具备教师资格的身分很严,必须是得到功名的秀才,会做做八股,写写行楷.吟吟诗赋,百无一是的书生。
这年三月,经国遵节随俗,穿一身棉布褂儿向孔子和祖宗牌位,规规矩矩地,行过三跪九叩礼,正式拜当地的周老夫子为师,开始他人生最重要的历程之一、典礼很隆重,读的课本更深奥,先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再“子曰:学而时习之”,就这么胡里胡涂,不知所以地,双脚蹒跚,踩到一个光怪陆离的知识领域。
地点就是本镇的武山学校,蒙师周东,可却不是《蒋总统经国先生人事年表》中所说的“奉化名贤”'1'念念天地玄黄,需要圣贤,未免要求过高。
第二年十二月,改业顾清廉,顾老夫子,一生靠砚耕为业,过去教过蒋先生,现在又教经国,所以毛思诚特为记上一笔,誉为“二世治教”。经国对他的几位塾师,包括顾以后的王欧声,从来闭口不提,倒是父亲的家教,赞扬备至。猜想,这些旧式塾师,对他不会有什么重大启发,以他自己的年龄,对经、史、子、学那套大道理,也不可能有所领悟。
我们姑且不谈蒋先生本人的行为德性,和他一身功过。他对儿子的教养,是下过很大工夫的,经国自己常说:“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是非常严格和认真的,不管在家、在外,都是经常来信指示我们写字、读书和做事、做人的道理。”蒋先生对儿子的期望,固然随环境的变迁,作适时的修正,但基本的方针和目标是不变的,那就是悉心培养,照他规划好的型模铸造。
蒋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局限,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南针。经国仅十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2'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常读《诗经》、《尔雅》。
蒋先生的两只脚一脚虽踩在革命的大道上,但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革命”就是狭义打天下做皇帝的新名词。另一脚停在封建残余的陋巷里,认为孔孟思想,将永远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尽管,他自己到过日本,喝了东洋墨水,却并没有真正呼吸到新时代的新气息,追求过军事常识以外的新知。因此,他还止步在明清儒学和旧礼教的境界里,冲不出去,甚至从未尝试。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在《我所受的庭训》一文中,经国有很详尽的描述:“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这难怪,蒋先生童年,就是这样造就出来的。他进一步解释读古书的作用时说:“你于中文,如能懂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孟庄骚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3'
他要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认为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汝在家,对亲需要孝顺”,而以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作为模范。甚至在政治上,也要师法曾国藩,作为“中国的政治家”。
只有和经国有过相同遭遇的读书人,才能体会到,这种了无生气,晦涩刻板的旧式教育,对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孩子,是何等不合理,对孩子止常心智的健康发展.是怎样的摧残!
保守的旧传统,在卫道者的眼里,是中国文化的伟大遗产,从某些角度看,它的永久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相对地,这个思想的根源,是封建的、是落伍的,甚至是反动的.和我们的时代是脱节的。所以,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以科学民主为先锋的新文化运动,即人们熟知的“五四运动”。蒋先生中了旧思想的毒,一生迷信四维八德的大道理是改造中国的万灵符,甚至被赶出了大陆,在台湾偏安,还在大喊文化复兴,强迫高中学生读《沦语》、《孟子》,还规定每年要祭孔。孔子的后代,可以坐在家里打着麻将领高俸,孔孟学会的招牌,也挂出来了。为曾国藩涂脂抹粉,装扮成伟大的圣贤豪杰。这种扒死人灰的意识形态,强加诸于他儿子的身上,进而加诸受他统治的子民身上,真做到了公私一体,贯彻始终。
所以,我们加以总结,在蒋先生的阴影下,经国旱年的教育,除了在四书五经堆里打滚外,并没有接受到当时欧风西渐现代教育的陶冶,塾馆生活,其实是些不堪回首的残梦。
一九二一年,溪口的蒋家发生了两件大事。
前一年的一月二十七.王太夫人扶病莅沪,和儿子聚到三月返乡,第二年六月,老太太沉疴不起,溘然长逝,这年仅五十八岁,蒋闻讯自广州赶回,已气息奄奄。'4'
母子情深,蒋先生的悲痛和孝思,悉在意料之中。由蒋自撰的挽联“祸及贤慈,当日梗顽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真情及乎词,一幅生动的写照。
经国顿失这位慈爱的祖母,而且来得这么突然,他的感受,缺文字记载,无从考据。曾为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伤痕和挫失,殆无疑义。
蒋先生和毛福梅的感情,一直不好,做孩子的,当能体会得到。感情再坏,王太夫人在世一天,基于老太太的威严,怕伤老人家的心,表面上,至少要维持一个夫妻的形式。
骤然间,这样一位中流砥柱的老太太去世了,结构上立即发生变化。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它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毋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望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人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子女者,如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父泐。”'5'
这个训词的真实性颇成问题,恐系出诸蒋的授意,由毛思诚事后补进去的,好掩饰以后他和宋美龄结合的合法性。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蒋的心态。现在又堂堂正正,假“革命”的大帽子,遗弃发妻毛福梅和如夫人姚怡诚。
果然,第二年和陈洁如在上海结秦晋之好,'6'他再去和汪兆铭、胡汉民,为自己“人人言弟为好色”去辩护,即无人置信了。
经国年纪轻,先有失去祖母的创痛,次有家庭破碎的震惊,那原是十的沉重的感受。可是在父亲面前,他能反抗吗?反抗又于事何补?
经国和母亲的情感,至深且厚,在他历年发表的文字中,虽少提到生母,怕刺激蒋夫人,伤到父亲的心,仅在江西时代出版的《我在苏联的生活》的自序中,吐露了他的心声:“回忆三十年来,始而寄迹海上,继而留学国外,长离膝下,十有余年。”他写着:“且因邮电不通,音讯久疏,母不知儿生死,因抑郁以成疾:儿亦未能亲侍汤药,以娱慈母之心。”毛夫人是一九三九年冬,为日机炸死,为了思念无已,出了这本书“用以纪念吾母,并志无涯之哀悼。”留苏期间,发表公开信,清算他父亲那一幕,用字遣词,比蒋的任何一位政敌,骂得还要无情和泼辣,但对母亲,始终亲情似海,未有半句不敬的话,与其说是至孝,毋宁说是出乎内心的同情和怜悯,是一种条件下的反射。
毛福梅算不上红颜,只能说是薄命。她是时代的牺牲者,典型的旧式女子,没有受过什么良好教育,和大多数她同一时代的女人一样,出生在闭塞的中国农村,假使和其它的女人一样,遵从父母的意旨,嫁个门当户对的庄稼汉,生儿育女,做个“三从四德”的好妻子,就能太太平平地过一生。不过,命运往往捉弄人,她的少女的幻梦,经不起时代的呼啸,给冲破了。前人的经验,“悔教夫婿莫封侯”,现在竟变成她自己的遭遇。夫婿非但郎心似铁,个性更粗鲁,动辄拳打脚踢,曾经有次,从二楼把她摔到楼下,对太太好比对士兵的办法。这些惨痛的往事、在犹是孩子的经国心里,他会做什么想法呢?
一九二二年的三月,经国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经过宁波到上海。他的心情很复杂,和母亲暂时告别,不免有些酸楚,武岭的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但是,上海的诱惑力很大,从父亲嘴里,不时听到关于上海的一切,那是个和奉化截然不同的新世界,父亲的事业,虽然由上海移到了广州,上海依旧是政治中心。这儿年在乡下读书,读来读去离不了塾馆那一套,实在厌倦了,听那些伯伯叔叔说,上海有新式的学堂,能换个环境,总是件好事。
三月的第三天,他考取了万竹小学的四年级。他过去念书的纪录,顾清廉的评语:“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先生自己的观察:“经儿可教、纬儿可爱。”那都是可信的信史。
经国到上海不久,蒋先生在虞洽卿的资助下,去了广州,且携美眷同行,即经国称呼她“上海姆妈”'7'的陈氏夫人。负责监护经国的责任,落到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身上,缺钱“则向舜耕(陈舜耕曾任台湾铁路局长)及果夫哥哥取”。'8'所以,和父亲还是分隔着的。
在上海念小学,精神、境界都为之豁然开朗,这年的下学期,初次尝试到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