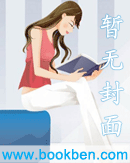应是屐齿印苍苔-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为我一直怀疑这种褊狭和机械的办法是否真正有利于抗战。①
任何伟大的事业,既需要轰轰烈烈,又需要踏踏实实;要有人奔走呼号,
也要有人坐下来埋头苦干;立足当前,放眼未来,高瞻远瞩,并蓄兼收。我
们抗战时期的精神积累,已属于历史范畴,当年的政策效应,何者为得,何
者为失,已不难根据实践的结果加以检验了。我想在此试举一例:目前我正
在读钱钟书的新版《谈艺录》增订本。此书初稿作于1940 年前后,内容与
抗战风马牛不相及,而作者称为“忧患之书”,在1942 年所写的序文里,
有如下的表述:
《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始属稿湘西,甫就其半。养疴返沪,行
箧以随。人事丛脞,未遑附益。既而海水群飞,淞滨鱼烂。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
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销愁舒愤,述往思来。
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掎摭利病,积累遂多。濡
墨已干,杀青鲜计。苟六义之未亡,或六丁所勿取;麓藏阁置,以待贞元。时日曷丧,清河以
俟。古人固传心不死,老我而扪舌犹存。方将继是,复有谈焉。
作者写作时的环境与心态,这里都说得很清楚。《谈艺录》于1948 年6
月问世,次年7 月出第2 版,以后不复再印。而海外风行,盗印不绝。直到
前年,才在国内经作者增订过半,重新出版。这是一部真知灼见,赅博精深
的新诗话,综揽古今中外的诗学诗艺,涉海探骊,攀梧引凤,抵隙披瑕,穷
根究柢,涉猎之广,造诣之深,眼界之高,腠理之精,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
“有一无二”的著作。苏东坡评《诗品》,说:“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
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正好移用于《谈艺录》。学海无涯,艺林丛
深,人事错杂,怎么能囿于有关或无关抗战,笼罩天地,执一以求呢?
嘘气成云,飞唾为雨,一窝风的习惯势力长期在我们生活里占着优势。
酷爱绝对化,不承认人的多样,世界的多样,事物的多样,不企求多渠道、
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多样统一。不相信“人之向善,谁不如我”这种
平凡的真理。热衷于举世诺诺,不容许一士谔谔。这种宿疾,该到下决心根
治的时候了。
这本现代散文序跋集,共收文585 篇,时间以1920—1949 为起迄。编
者的方针是求全。全,就必然杂,难免挟鱼龙泥沙、精华糟粕以俱下。但这
也有好处,因为有了比较,才能于杂中见纯,纯中见杂;低中见高,高中见
低;劣中见优,优中见劣。纯是经过澄滤的假象,杂才是本相。我希望读者
能由此较为清晰地看到昨日文坛的一角,并及于昨日世界的一角。
1986 年7 月11 日
梦中说梦 ——《八十年代散文精选》序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了一部《八十年代散文精选》,嘱在卷首缀以片言。
我近年来很想痛下决心,摈绝别人命题作文,包括代人写序。因为我自知不
擅此道,写时也很窘苦。可惜我意志薄弱,进退揖让的结果,还是同意勉为
其难。拖了许久,主编很委婉地来信催促。我花了3 天时间,把五百多页的
清样读完了,很高兴有机会读到那么多好文章。但临到动笔,却又十分踌躇,
觉得难于措手。
不知怎么,忽然想到了梦。记得人民日报出版社的“百家丛书”里,有
一本巴金同志的《十年一梦》,是《随想录》的选本;不久前在报上读到一
篇文章,题目也是《十年一梦》。不过前者指的是“文革”十年,是旧梦;
后者指的是改革开放的十年,是新梦。沿袭我们的习惯用语,前者意在“暴
露”,后者意在“歌颂”。《散文精选》是80 年代的作品,属于后十年范
围,但千丝万缕牵连着前十年,乃至几十年,新梦套旧梦,旧梦套新梦,欲
说还休,欲休还说,剪不断,理还乱。
梦与觉、醉与醒、幻与真、虚与实、显与隐、形与迹、光与影、暗与明,
都是生活里一事的两面,互相依存,而泾渭自分。第一个把水搅浑的是庄周:
“昔者是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
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人即胡蝶,胡蝶即人,后人就渐渐的
把梦与人生混为一谈,什么“浮生若梦”,“一场大梦”,“事如春梦了无
痕”,“百岁光阴一梦蝶”,一发而不可收拾。
梦与文学确有一脉相通之处,文人大抵爱做梦,创作本身就带有梦的意
味。唐诗宋词,“梦”字几乎被用滥;历代小说笔记名作,梦话连篇,以梦
为书名的也不少;汤显祖以“玉茗堂四梦”著名,说明梦富于戏剧性。“礼
拜六派”有一位小说家,干脆以“海上说梦人”为笔名;张恨水写过《八十
一梦》;“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刘大白的第一本白话诗集,命名《旧梦》。
但到了30 年代,形势一变,梦开始遭忌讳,梦与现实,俨如唯物唯心的天
堑,壁垒森严,不许越雷池寸步。何其芳以《画梦录》名噪一时,害得他后
来自怨自艾,忙不迭自我检讨。施蛰存因为推荐文学青年读梦化胡蝶的《庄
子》,受到鲁迅的批评,退却时又拿庄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话
打掩护,落得倒霉几十年才翻身。鲁迅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毕生刚正,严
分是非爱憎,决不肯含糊半点。但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看够了这几十年间的
是是非非、唯唯否否、亦是亦非、亦非亦是、忽唯忽否、忽否忽唯、颠来倒
去、倒去颠来,不知有何感想?或许也不免喟叹前尘如梦,以自己的过分认
真峻切为憾吧?
据说至人无梦,而芸芸众生,终不免为梦所苦。梦是相思的止渴剂,痛
苦的逋逃薮,希望的回音壁,补天的五彩石。可惜良宵苦短,好梦难圆;春
梦无凭,恶梦却常常变成事实。梦中得意,醒后成空,南柯梦和黄粱梦是世
人熟知的故事。被失望折磨过久,难得碰巧有点好事,反而会疑心自己在做
梦,不相信是真的。我做过无数的梦,早如游丝飞絮,了无影踪,只有一梦
特别,没世难忘。“文革”初期,我就被投入监狱,侘傺悒郁,经常乱梦颠
倒。有一次梦见和熟朋友欢聚,自在逍遥,快若平生。我忽然明白身在梦里,
惊呼:“这是一场白日梦!”此情此景,真是太悲哀了!
梦有长短,生理学的梦很短,心理学的梦却很长。美国科学家发现人做
梦时眼球会快速跳动,根据这种生理现象选了一大批人做实验,测定最长的
梦历时2 小时又23 分钟。心理学的梦却动辄十年几十年。“文革”茫茫十
年,人心望治,如大旱之望云霓,但当时有一种权威的预言,却还说以后每
隔七年八年就要来一次,不禁使人想到《西游记》里的唐僧,没完没了的九
九八十一难,一忽儿盘丝洞,一忽儿火焰山,不知何年才到得西天?美国作
家欧文有一篇小说,描写有个乡下人入山打猎,倦极而眠,一觉醒来,已经
过了20 年,回到村子里,满眼陌生人,世界大变。中国也有类似的传说:
晋代有个樵夫上山打柴,遇到两个童子下棋,放了斧头作壁上观。一局未终,
发现斧子生锈,木柄已经烂掉,回家后山川依旧,人事全非。原来那两个童
子是神仙,樵夫只睁着眼做了个短梦,“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世事
也正如奕棋,如果能在不知不觉无思无虑中瞬息嬗变,像电影里的叠化镜
头,人间真有这样的梦,倒也痛快,省了许多苦熬究捱,痴心妄想。
中国传统奉散文为正宗,如果把《论语》、《孟子》、《道德经》、《南
华经》都算上,直到《梦溪笔谈》、《陶庵梦忆》、《阅微草堂笔记》这类
作品,真是浩浩如长江大河,注之不盈,汲之不竭。但“文革”十年,散文
河底朝天,土地龟裂,一睡沉沉,成为不毛之地。进入改革开放的十年,才
如梦初醒:一夜江边春水生,洪波细浪,激荡推涌,洋洋洒洒,映照出这时
代生意盎然的一面。这散文百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聚会,就是很好的印
证。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写神仙无心出错,闹了一回恶作剧,
在雅典城外的树林里,把两对情人耍弄得神魂颠倒,爱恶错乱,啼笑皆非;
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我们也演了一出《仲夏夜之梦》,没有莎
士比亚式的浪漫,却十分惊心动魄,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
开始。散文的前景如何?神仙大概知道。
五代是长短句发荣绚烂的时代,南唐这个小朝廷里,就不乏词坛高手。
有一次李璟和冯延巳君臣谈词,冯延巳很赞赏李璟的名句“细雨梦回鸡塞
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李璟却引冯词《谒金门》中的隽语,笑问:
吹皱一池春水,于卿底事?
散文荣枯,于人底事!梦中说梦,聊以应命:是为序。
1989 年8 月26 日
(本文为《八十年代散文精选》序言)
报幕 ——查志华《无华小文》序
海有多宽,地有多厚,森林有多深邃,城市有多壮丽,色彩有多绚烂,
音籁有多丰富,——地球有多大,散文的领地便有多广。
但人生有涯,个人的天地窄小得可怜。
地球不是世界的全部,只是四时运行、历史演变的舞台。文明与野蛮,
繁荣与贫乏,战争与和平,专制愚昧与民主自由,爱与仇,欢乐与痛苦,正
直与邪恶,幻想与现实,心灵的颤动、搏击、探索、拥抱,才是散文广袤无
边的沃土。
圆颅方踵之伦,大体形似,差别万千。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写过一首生前
未发表的诗:
“我们”这个字眼我总信不过,
没有人能指着另一人说:“他就是我。”
协议背后总有些事情不大可靠,
外表的一致掩盖着鸿沟一条。①
人不分男女老幼,肤色种族,有人类共同的本性,共同的倾向,例如对
美,对光明,对真理,对公平合理的追求;人际关系中有共同的珍宝,例如
宽容,谅解,友爱,团结。但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人,尊严不容亵渎,人权
不容侵犯,意志不容予夺,名器不容假借。矫揉造作的“一致”只是自欺欺
人。散文家如果不能做到我就是我,他就是他,千百个等于一个。——不,
加起来等于零。
在新起的散文群落中,查志华同志有自己的世界。——她用自己的眼观
测,自己的心映照,自己的手描画。这世界也许不够庄严华妙、涵盖万有,
但确是她自己的园地,打着她鲜明的标记。
宋代有人拿柳永和苏轼的词相比,说柳词“只好十七八岁女子,执红牙
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词“须关西大汉,绰铁板,唱‘大江东去’”。
志华是女作家,笔底却洗净铅华,摒绝搔首弄姿,“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她咏叹的是质朴的人生,从平凡中体现高大,短暂中抉发永恒,琐屑中揭示
隽永,喧嚣中探求静穆。宜于良朋二三,清茗一壶,纵心随意,娓娓而谈。
她不拘泥于散文的概念、形式和藩篱,如行云流水,行其所当行,止其
所当止。笔致清朗、时有隽语,坦率中不乏芒刺,在流行的时风中自成一格。
散文的本质是以心会心,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