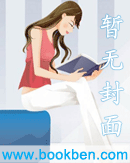应是屐齿印苍苔-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才有些亲身的体会。宪兵队在贝当路,人们谈虎色变,讳言其名,称之为“贝
公馆”。地点在美国学堂旧址,原来是雪白的建筑,碧绿的草地,纯洁得像
天使;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教堂,紫酱色的斜屋顶,墙上爬满长春藤;贝
当路幽雅安静,是情侣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挑选这么
个环境来开设他们的现世地狱。我被释放时,恰像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对那
个环境感觉特别灵敏,觉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里,又看到张爱玲的留言,
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
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这
事情过去整40 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机会读到《今生今世》,发现其中有
这样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
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
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
这样一回事。一时间我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在此以前,我刚好读过
余光中针对胡兰成的人品与文品而发的《山河岁月话渔樵》。抗日战争是祖
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胡兰成的言行,却达到了颠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极致,
余光中对他严正的抨击,我有深切的共鸣。因为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
的论据。但是对张爱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
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言,1944 年8 月)
张爱玲是敏感的,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战火依
然弥漫神州大陆,的确是“更大的破坏”,但破坏不等于毁灭。古老中国和
她的儿女,都在经受水深火热的考验。——张爱玲也在经受考验:内外交困
的精神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的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
就像放电影断了片。
1949 年,在张爱玲看来,对她无疑是灾难。但事实不像她设想的那么坏。
抗战胜利初期对她喧闹一时的指责早已沉静,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吸引着亿万
人的注意——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了。1952 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
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
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
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
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
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
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任何事物都有复杂性,不像一般
观念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左翼阵营里也不乏张爱玲的读者,“左联”元老派
的夏衍就是一个。抗战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
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第一号的领导人物。
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夏衍从不讳言自己爱才,但用
“左”视眼看起来,也就是“右倾”,“温情主义”。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
成立,夏衍亲自兼任所长,我被委任为他的副手。他告诉我,要邀请张爱玲
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我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
就听说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后来夏衍调到文化部
当副部长,我还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到北京
去送给他。
生活是个谜,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着许多秘密和未知数,何况是身
外冷暖,背后文章;加上彩凤折翼,灵犀失明,大陆长期与世隔绝,被海外
视为“铁幕”,彼此缺少了解,也就无怪其然了。
人没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点一滴的经验,常要用痛苦作代价,
这就是悲剧和喜剧的成因。时间蚕食生命,对老人来说,已经到了酒阑灯灺
的当口;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也因此能够看得宽一些,懂得多一些了。—
—真要明白,当然不见得,老糊涂多的是。专门研究张爱玲的唐文标教授,
说“张爱玲写作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她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可说
是阴差阳错,也许亦是她自己所决定的。”这话说得好,但也还可以推敲,
因为同实际有距离,原因也是由于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倾城之恋》里的一
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
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
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流苏并
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
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
设。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
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30 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
——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
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
传统,好处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
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
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
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
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
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
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
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
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
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张爱玲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足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
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这绝不等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
所认识”,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
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
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1984 年1 月,我在香港,以鬯伉俪赏饭,座上有梅子、黄继持、郑树森,
茶余酒后,谈到了张爱玲。我说她离开大陆,是很自然的事,对社会主义感
到格格不入,不合则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国内曾经“运动”成风,
到“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点,张爱玲留在大陆,肯定逃不了,完全没有必
要作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为此代她庆幸。但对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
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不像出于《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作者的手笔,
我很代张爱玲惋惜。并不因为这两部小说的政治倾向,我近年来有一种越来
越固执(也许可以说坚定)的信念:像政治、宗教这一类有关信仰的问题,
应当彼此尊重,各听自便,不要强求,也决不能强求。谁如果确信自己的理
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别人反对。《秧歌》和《赤地之
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
去作者原有的美。无论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于虚假,就必定导致在艺术
上缴械。张爱玲在这两部小说的序跋中,力称“所写的是真人实事”,而且
不嫌其烦,缕述“故事的来源”,恰恰表现出她对小说本身的说服力缺乏自
信,就像老式店铺里挂“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一样。事实不容假借,想象
也须有依托,张爱玲1953 年就飘然远引,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
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这里不存在什么秘诀,什么奇迹。海外有些评
论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恋》赞得如一朵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
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但这种暴露也是肤浅而歪曲
的,在国内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新社会不是天堂,却决非地狱。只要有
点历史观点,新旧中华之间,荣枯得失,一加对照,明若观火。现在中国正
在吸取过去的教训,满怀信心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可以告慰于真正悲天悯
人、关心祖国休咎的海外同胞的。
三十年风驰电掣般过去了,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我多么期待能看到
她新的《金锁记》,新的《倾城之恋》。——“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
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
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
的祝愿,亲切的问候。
1984 年11 月22 日,
完稿于北京颐和园左近
《台湾散文选》序
《中国近代散文选》为台湾诗人兼散文家杨牧先生所主纂,经营两载,
上起“五四”至30 年代诸家,下迄台湾当代作家的作品,遐搜博采,洋洋
大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把其中台湾作家的部分,酌加调整,命名《台湾散
文选》,移栽于大陆。近年台湾作家的小说,已有不少络绎渡海内来,有的
已搬上银幕荧屏,诗也有了一些,而散文的荟萃问世,还是第一次。我有一
种私见,以为在各种文学形式中,散文最具直抒胸臆的特点,便于心灵交流。
今夕何夕,共此烛光,海峡两岸,蒹葭苍苍,也实在参商太久了。
中国自古为散文渊薮,源远流长,“五四”时代内经新潮涤荡,外受西
风吹拂,在文学革命运动中先声夺人,成绩最为绚烂。70 年来,名家辈出,
百体纷呈,孳乳繁衍,已形成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文体。而世事惊涛,席
卷天地,影响所及,散文的曼衍起伏,曲折正自不少。作家感觉敏锐,愤世
忧时,致使腕底风雷郁结,文格偏于峻急,是很自然的事;而散文这一大河
中的支流分派,因缘时会,或逐浪而奋飞,或因势而变风,或谢时而芜秽,
互为消长,也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文学是人类精神升华的表征,政治的辐
射,时局的动荡,难免吹皱一池春水,但政治自政治,文学自文学,强使合
流,等于焚琴煮鹤;此中况味,感受已多,现在潮平岸阔,月白风清,正是
洗盏更酌的时候了。
《台湾散文选》共收34 家的作品,计73 篇,30 余万言。庄容隽语,婉
喻微讽,玄思遐想,抒情感怀,体貌品类,大致具备,而通体整齐和谐,显
示选家谨严的识力和作风。编选体制中有个特点,是循古人编选诗文总集的
成例,每一作家,文前系以简明的传历,便于读者人文相印,增生亲切感。
入选诸家,从年龄看,与“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