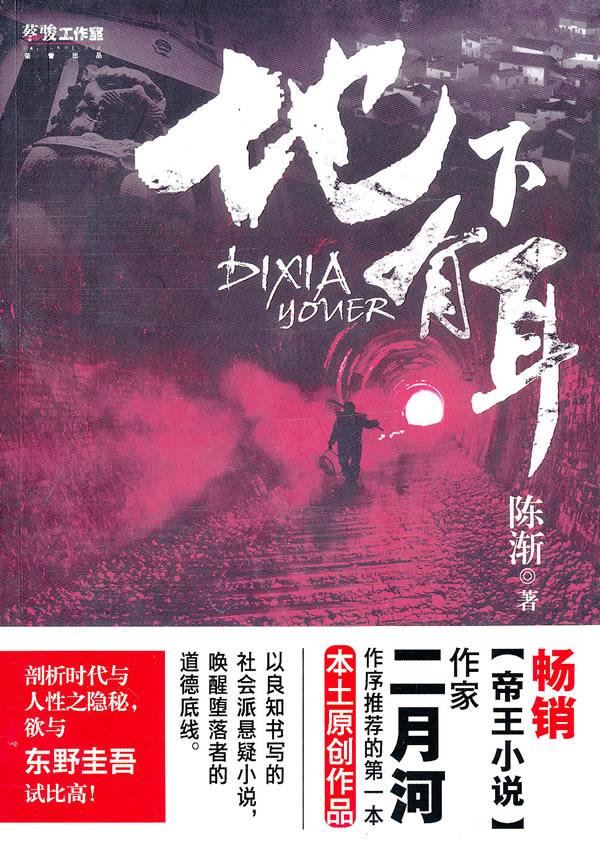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1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向他借了二十公斤,”塔拉先科说。
“那就更奇怪了,”耶戈罗夫接着说。“整个这段时期中只有一百八十公斤……如果按照巴利茨基的定额来计算,每一列车需要十五到二十公斤……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好了,到当地再说吧。耶戈罗夫同志,您留在这里吧……”
我跟同志们告别以后便耸身上马,并且叫通信员走得快些……
我常有机会到大规模的联队和不大的支队里去。他们在有些地方彼此都相似。他们首先会在哨所上拦阻你,检查一下,然后你顺着踏出来的小路走到营地去,而在指挥部的帐篷或地下室的附近,你会看到人们来来往往,行色匆匆。如果是夜里,象现在这样,那么在篝火边就有些值日人员或坐或靠在那儿聊天。指挥员会跳起身迎上前来。
而在这里,我们已经闻到了一股篝火的烟味,可是到现在还没有看见哨所。
通信员姓加尔布晋科,突然响亮的说:“请您等一会儿,我来把绳子拉紧了,要它不出声……”他下了马,很有把握地走进森林的暗地里去,并且长久地在那里忙些什么。我跟着他走去。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往深里拉着一根降落伞的绳子,绳子上挂的是空罐头。
加尔布晋科向我说明,这个设备直通着指挥部。我拉了一下,罐头响了。
加尔布晋科立刻吹了两声拖得很长的和一声断断续续的口哨声。
“真的可以吗,将军同志!这立刻就会有人开枪打死你!”
这时我们听到了树枝的噼啪声和口哨声。不一会儿,在篝火的亮光中出现了一小队人。走在先头的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穿着一件黑色的党卫军的大衣,腰间束着一条宽皮带,皮带上挂着两颗手榴弹。按照游击队的规则,右肩上挂着冲锋枪,枪口朝下,头上带着喇叭口式的德国新钢盔。奇怪的是这些讲究穿过着的军人的脚上都穿着草鞋。可是我已经知道,克拉夫琴科强迫所有到铁道上去的人都穿这种鞋子。也许因为篝火的光线照射着吧,小伙子们的眼睛都炯炯有光。全队站定了。小伙子向前迈了两步,用立正的姿势敬里礼。克拉夫琴科迎着他们站了起来。
“指挥员同志,”小伙子欢乐地大叫道,“发亮了!”
我认出这个小伙子是耶罗欣。噢,不错,正是他。他由于不守纪律被第五大队免了职。我从来没有想到会看到他是个爆破队的队长。
“恭喜你!”克拉夫琴科开始说,但是突然顿住了。“这怎么啦?”他指着站在耶罗欣身边的战士说。那位战士挟着装炸药的小箱子。“队长同志,请您回答我,为什么没有埋设地雷?”
“没有来得及……”
“好,休息去吧。以后再谈。”
耶罗欣把自己的小队带进林木深处去了,不一会儿,那里第二堆篝火噼哩啪啦响起来了。
“菲佳,你为什么不满意呢?”我问,“您瞧,这个小伙子多了不起!我跟政委还认为他不行呢。”
“我现在也是那么想。”
“但他不是炸毁了军车吗……不能责备胜利者……”
“应该责备,他这样炸军车已经是第二回了……”
克拉夫琴科把自己的制度讲给我听。爆破队首先应该把往前推算几天的定时地雷埋好。除非时间有多,才打正在通过的、这种现在很少的夜车。
“他只为自己着想,为了给他记上一列军车的帐。抓住了一列,却失去了五列。自己没有埋地雷,也没有给别人埋……”
我们还谈了好久。克拉夫琴科把所有炸毁了的二十三列军车的原来的指令给了我。联队司令部的同志们后来进行了必要的检查,虽然这样的检查已经没有特别必要。
拂晓时,所有的爆破队都回来了。支队政委纳克斯也随着其中的一队来到了。他是一位高大的、善良的人,二十四、五岁年纪,从前是教员。他好像顺便地敬了礼,用自己那双温暖的大手把我的手摇晃了很久。
“现在我们游击队员的工作变得很有威力了,”纳克斯呷着咖啡说。“弟兄们都很好,无须着急。我和菲佳有时侯训斥训斥他们,可是一般说来,他们自己都很努力:还是竞赛,而且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战斗中也没有那些印象。军车,这是具体的对象!我们的弟兄们在努力。现在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按照头等的精确性在工作。费多罗夫同志,我完全有把握,如果您作为一位作家在早晨顺着我们在夜里埋了地雷的铁道路基走去,一定发现不出来!这样的工作才使我满意!”
看来,他很喜欢使用“工作”这个词。就我所记得的,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作战”这个词,而一向是说“工作”的。
“政委同志,你们这儿的政治工作搞得怎么样?”我在动身以前问他道。
“没有什么,费多罗夫同志,我们在工作啊。您要是愿意的话,我们今天去看看也行。不过和切尔尼多夫的地下活动有些不同。我们这里是公开的。一到闲空的日子,我们全体队员就到当时在我们旁边的村子里去,和农民们一起割草。而现在有别的工作——挖马铃薯。有这样的说法:‘红军快要来了,应该排挤富农,而把贫农和中农团结起来。战后集体农庄的事业会巩固的多,’……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将军同志……”
当夜我就动身到联队司令部。一路上,我考虑着许多事情。
克拉夫琴科支队一共不过六十二个人,其中有五十五个是没有经验的年青人。我们甚至不相信这些未经训练的小伙子会爆炸军车,哪怕是一裂。事实上他们在不足一个半月中间所爆炸的军车,按每一名游击队员来计算,比所有其余的游击队员都多。
我在克拉夫琴科那里所看到的一切,迫使我用新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全部工作。我和省委会和联队司令部的同志们,包括爆破工作的专家们在内,都知道运用定时地雷和一般的地雷爆破新技术会增加列车事故的数字。可是直到现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人知道什么意味着多,什么意味着少。
根据去年的经验,我们认为巴利茨基大队达到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克拉夫琴科运用了与众不同的战术,这样的突飞猛进,使巴利茨基远远地落在后面了。
问题不仅在于克拉夫琴科和支队政委纳克斯善于不论在什么时候吸收和训练年轻的农村青年,拿这个来证明“事在人为”。不,克拉夫琴科用自己的经验证明没有必要去袭击列车,没有必要每天会战。他表明了才干和组织性能够比有勇无谋带来更大的效果。
就地了解了克拉夫琴科的活动以后,我看到了巴利茨基的大队做得根本没有那么多。在克拉夫琴科那里每两个人炸毁了一列军车,而在同一时期中,在巴利茨基那里却是十个人炸毁了一列军车。
……第二天晚上,我回到了洛勃诺耶。同德鲁日宁和雷先科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在九月初召集地下省委开会,并邀请全体大队指挥员参加会议。
第五章 地下省委大会
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在省委召开大会的那一天,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大队指挥员,许多政委,党、团书记。在这个值得我们纪念的日子,最先来到洛勃诺耶的一个人是巴利茨基。
关于他的来到,我是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的。
中央营地里沿用了惯例:如果我们大队的指挥员们或是和我们邻近的支队的代表们中有人来到的话,哨所就把这件事通知了无线电中心,而马斯拉科夫便从那里通过那些挂在所有十字路口的树上的扩音器把这件事广播出来。
到巴利茨基来的那一天,他的大队已经翻毁了五十六列敌人的军车。
我走出去迎接他。
我们骑在马上彼此握了手。他有一种粗心浮气的优越感,脸上洋溢着自负的表情,似乎早先从未有过。可见用无线电广播的郑重的通告,很合他的心意。
“来,格里沙,”我向他提议道,“咱们到营地里去跑一圈。你不是好久没有到这里吗?咱们去看看军需处,然后吃早饭。我要请你尝尝我们自己做的香肠。你听到过游击队员有自制香肠这样的奇迹吗?”
“你们在积草囤粮吗?”他带着讽刺的意味说。
巴利茨基骑在马上,就象一名真正的骑兵,远不是战争第一年的模样了。在他皮制的短外衣上,挂着少校的肩章,胸口别的是苏联英雄的金星和列宁勋章……斜皮带,木壳里放着毛瑟枪。在极好的、擦得精光闪亮的马靴上带着踢马刺。是真正的、雄赳赳地指挥员的外貌。
我们跑近了医院的白色大帐篷。格尼达什走出来迎接我们。
“你们认识一下……”
巴利茨基把手递给格尼达什,没有下马。
“外科医生同志,你把我们的伤员搁得太久了。”
“您的伤员最多,并且伤得都很重……”
“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外科医生同志!我们无论如何不可能没有伤员……今天你听到了,已经是五十六列军车!不论是什么军车——都得战斗,冲锋。你瞧,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啊!”
巴利茨基不带明显的兴趣,对大橡树底下和自己的桌子排成一行的鞋匠们瞅了一眼,又对坐在另一些橡树底下的裁缝们瞅了一眼。见了舒勃尼科夫,他笑起来了。
“这是干什么,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
“格里沙,慢慢地准备过冬啊。天气一冷,大概你也要件皮袄吧?”
“我看不到那么远。”
“这倒是真的,你不是喜欢向前看的人……今天我们要在省委会议上听听你的意见。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同样要谈谈怎样向前看的问题。”
“我要坚决地提出一个问题,费多罗夫同志。”
“这是你的权利。”
“我那里一共只剩下了七公斤炸药……”
“我们在省委会议上再谈,现在我们吃早饭吧!”
巴利茨基跟克拉夫琴科在司令部的帐篷里相遇了。他们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就没有见过面。我以为这种相遇会亲热得多。但是巴利茨基却带着首长的宽容口吻说话。
“你不愿意到我那里去,菲佳。当心,你以后要懊悔的。”
克拉夫琴科带着敷衍的微笑回答道:“规模不一样呀!”
吃早饭的时候,巴利茨基讲了一段很精彩的故事。
大约一个月以前,在“卸货战役”以后,游击队员们已经迫使被炸毁的军车上的护车队沉默,把车上所有能拿走的东西全都拿了,放火烧了车厢,开始往回走,这时从脱轨机车的翻倒的煤水车里发出了一阵绝叫:“康姆拉德,康姆拉德!”(德语:同志)
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身上穿着战时铁道员工的制服,双手尽量举得高高地站在煤水车上。
他们把他带了下来,叫他驮了一袋从车厢里弄到的高统靴,给带到营地来了。
在那里借翻译员的帮助,他说,在这条干线上充当火车司机已经快一年了。在最近两个月中,他在游击队的地雷上经受了十六次倾覆事故。每次当火车开近危险地区时,他就把助手留在机车棚里,而自己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