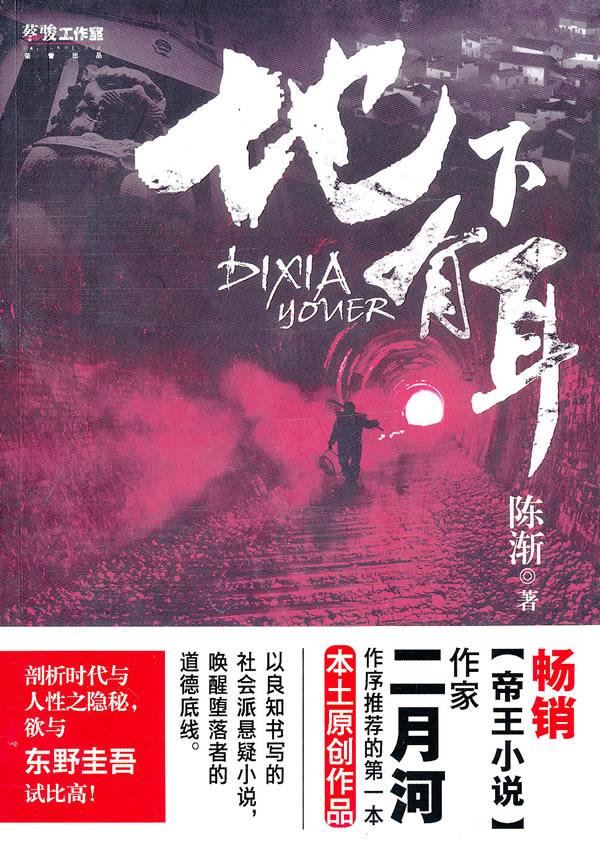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甚至后来,在雅勃隆诺夫卡会议以后,在波略丁的混乱以后,在很多天的单身流浪以后,我还有这样的想法:只要一到达切尔尼多夫省,到得省里的任何一区,我立刻会遇到布置在各个岗位上积极活动的那些人员。
然而,当时我们以为德寇会在占领地区很快地组织起来。我无论如何想不到会能够在青天白日之下公然沿着大路走;不但沿着大路走,而且还沿着村街走。我想,隔不了两小时就得乔装改扮,我想,暗探们会监视我,而我得用尽一切非常机巧的方法牵着他们鼻子瞎跑一阵……
为游击队事先准备的根据地、地下区委书记们的决定和地下集会场所的组织,起着极大的作用。绝大多数留下来的地下工作人员,从最初的那天起就开始行动了。不过工作和环境却和我们事先想象的完全不同。
比方说,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地下工作者应该花相当时间去熟悉和习惯新的环境,而且连自己最熟悉的人都必须重新估定,按另一种方式跟他建立关系。我们也没有估计到,地下工作者会一开始便见到德国人,一开始就得隐蔽起来,一开始……是的,他一开始看到和打听的事情是不胜枚举的。
我们也必须懂得,留在地下的共产党员都曾在苏维埃时代担任过领导的职务。有些人职位较高,有些人职位较低,可是大多数还是本区有名望的人物,一出了什么事,小孩子都指得出他们;而且不仅是小孩子,集体农庄的女庄员也可能随随便便地走来直呼他们的姓名……
因此,地下工作者在初期与其说工作,不如说体验,而且每一个人都必须忍受相当时候。时间的多少,全看这个人的性格而定。要是这个人和团体一起留下,那他便容易通过这些苦难,假如是单独一个人,就比较困难了。有些人简直害起……迫害狂病了。
我们放下一般的议论不谈。我早已把自己的体验写得非常详细。老实说,那时候我真对他们厌烦了。
我开始找区委第一书记普辽德科同志,和前区委执委会主席、现任游击队司令员的斯脱拉盛科。
我在西斯基村偶然遇到党区委组织部的前部长皮洛夫斯基。我不打算描写我们的相逢。他平平常常地接待了我,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了我。但可惜他知道得也不多:他不过比我早到这里一天。他曾在基辅附近的什么地方被围,就流浪到家乡来看妻子。皮洛夫斯基没有留在此地的意思,他跟西蒙年科一样,一心一意只想回到前线去。
皮洛夫斯基早就想去找区委书记,他听人说普廖德科已经把家眷疏散,放弃了秘密住所,正和执委会主席斯托拉盛科一起在到处流浪。
本区似乎有一个游击队,但这时没有听到它什么消息。
“似乎……也许……在某处……到什么地方……”这种指点,不能使我满意。我谢过主人,便上干草棚睡觉去了。
我疲倦极了。上一夜走了许多路,和‘浸礼教徒’互相射击,和库尔科辩论,直到白天也没有歇息。我似乎睡得很熟——好象被打死了的一样。然而不知是干草御不了寒呢,还是我神经过敏,我总是怒气冲冲。事实上,到什么地方才合适呢?我走过四个区,没有碰到过认真地组成的地下组织。我反躬自问了:“那么怎样才算是认真地组成的地下活动呢?”在切尔尼多夫的时候,所有的密码、所有的暗号、所有的接头地点都曾得到我的同意。当然,我记不起每一个人;但我认得区组织的书记们,而且在进入德寇后方以前,我已拟定到波布特连科的省支队去的大致的行军路线。在这条路线上又有秘密住所、又有人名表(不是姓名,而是只有我能了解的确图例。)
但是我不得不多少改变了自己的路线,而我的一些记号和某些必要用来确定方向的手册,已和我的地图夹一起葬送在麦诺哥河底了。
这是我个人的失策,也是一件难于预料的偶然事故。我有什么权利来抱怨没有碰到地下组织呢?可是博契科呢,来自伊格那托夫卡的同志们呢,难道他们不是地下组织的成员吗?我对于库尔科的行为是愤恨的,恨他没有一件事知道得清清楚楚。莫非区地下组织的领导上大概已经知道库尔科的“家庭纠纷”,因此不让他知道自身的行动和计划吧。
我一面躺在干草棚上冻得直瑟缩,一面这么思索。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如果大计划经过深思熟虑,面面俱到,那么个别的人员,甚至是相当大的小组的失败和‘偶然事故’,也并不可怕。
地下省委的大计划中曾规定:每区要有一定数量的基层组织,各居民点要有一定数目的秘密住所。这个大计划已经实现了。凡是有区组织的地方就有秘密住所。当然,地下工作人员并非总是碰到任何“家庭戏剧”的。但是秘密住所并不是有食堂、现成茶水、时钟和其他车站特性的火车站,能够了解到这一点是好的。
避免跟敌人见面,是每个地下工作者或游击队员的个人经验的事情。我从前方到省支队一路所获得的经验,后来对我极有用处。我学会了步行、学会了观察和倾听。我懂得了地下工作的技巧是要了解‘偶然事故’的本质,要使‘偶然事故’也转而有利于抗敌斗争的大计划。
我把地图夹踏入麦诺哥河的粘土河底这件事,自然没有使我误入迷途。我熟悉我们切尔尼多夫省里的任何一条小村道和任何一座农庄,虽说不是每一条小路。我有了接头地点的地址,本来早就可以找得到自己人的。但是拖延对我有利。我切近地熟悉了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知道了人民的心情,学会了对不同的人们随机应变……
我又辗转反侧了好久,最后快要开始打磕睡的当儿,忽然听到了什么人的脚步声和谈话声。我侧耳细听,立刻明白那谈话与我无关。我把帽子拉下来盖好耳朵,想睡得安稳些。但仍与世无补,睡意消失了,我不知不觉地偷听下去……原来是一对爱人。
在我躺着的草棚附近,有一条相当入画的小路在灌木从中蜿蜒而过。这一天晚上,月色皎洁,没有云,不过风仍在狂吹。从这对爱人的声音来判断,他们年纪大约是二十上下,最初在我隐藏地方附近时隐时现,后来就靠近我坐定下来。
“我们多不幸啊,”姑娘说。“要不是战争,我们已经把房子完工,拿到酬劳,而且搬进去……”
“噢,”小伙子表示同意。他多半把自己限定于这些简短的意见,有时还打断女友的话去吻她。然而,这并不妨碍她发言。
“听着,安德列,”她用那种十分甜蜜的声调说。“等你最后从战场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去登记结婚吗?”
“当然喽!”
“象卡尔品科家那样的收音机,我们要买一架吗?”
“噢……”
“你让我到师范学院去学习吗?”
“在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吗?”
“不,在切尔尼多夫。”
“只有在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那里有一所冶金技术学校。师范学院每一个城市都有。我上冶技去,你进师范……”
“不,安德列,让我们一块儿到切尔尼多夫去吧!”
这两位年青人似乎完全没有现实的感觉。他们带着那种自然而然的信心,谈到自己未来的学业,好象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沦陷。他们到切尔尼多夫去,还是到德涅泊彼特罗夫斯克取得辩论,持续了好一会儿。显然是一段很常德时间。双方没有取得协议,于是姑娘便换了话题。
在再一次接吻以后,她用甜蜜的嗓音问:“安德列,你爱我吗?”
“那还用问吗……”
“你亲自带我去吗?”
“我要派飞机来接你。”
“不,说真的,安德列,别开玩笑,你捎个信来,我自己会上你那儿来的。安德列,我也是个共青团员呀。告诉你的司令员:就说有个好姑娘,她会开枪,会做甜菜肉汤,会照顾伤员。”
谈话变得越来越使我感到兴趣。我竟想爬出去,老老实实地问他们打算上哪个游击队,那个队伍配置在什么地方,再顺便打听以下,它有了多大的成就。但是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认定,若是那么做,不是叫他们大吃一惊,便是——如果小伙子还有点胆量的话——可能自讨一场没趣。而且我从以后的谈话中明白,他并不是个胆小鬼。
也不知是我微微动了一下,还是什么不相干的声音传到了这对爱人的耳朵里,那姑娘忽然惊起,以惊惶不安的嗓音央求安德列赶快离开。
“哦,安德列,我心里老觉得不安。他们怎样拿刺刀刺你的好朋友啊。他们骑着马,他是步行的。他们追到屋子里,叫声‘搜’!就把刺刀刺进他的肋骨……”
“他不是我的朋友。假如给我一条扎实的皮鞭,我会恨恨地揍他一顿。”
“可是德国人同样枪毙了他。要是他在德国人一边,他们决不会枪毙他……”
“因为找不到我,他们便怀恨在心。要是他把我送给了德寇的司令部,他们决不会枪毙他……”
“噢,这位情人原来是这样一个人。现在我只想爬下去握一握他的手。”
今天皮洛夫斯基的妻子告诉过我一件意外的事情,那件事是昨天早晨在邻村发生的。我没有留神听她。那时我以为她说的目的是想嚇唬一位不速之客,快点儿摆脱我:她说这里是不安全的。但是现在看来,她并没有捏造。
我从这对情人的谈话中,听出了这个故事的若干详情细节。安德列虽然由于谦虚,或者为了不谈不愉快的事情,故意避免读到这个题目,但是不管怎样他和未婚妻回想了多多少少小事。
事情是这样的:一小队德寇在奥尔沙内村拿住了两名红军战士。其中一个便是安德列。
德寇看中了这个村庄,在那里盘踞了几天,叫居民供给他们吃喝。这两个被扣留的俘虏被迫做着一切最肮脏、最令人厌恶的奴仆式的工作。德寇吃醉了酒便鞭打他们,侮辱他们,而且一分钟也不让他们不在眼前。
昨天早晨,伍长派了一个德国兵押着这两个俘虏到顶楼上去找‘柴火’。那个兵给了安德列一把斧头,叫他砍下叉梁。安德列不去砍梁,却用斧背敲了一下德国兵的脑袋,抓住他的手枪,对同伴喊了声:“快逃!”
但是对方却捉住了安德列的胳膊,叫唤德寇。安德列对这位‘朋友’狠狠地踢了一脚,挣开身子打天窗跳了出去。等到德寇发觉,安好马鞍,安德列已跑出村子半公里了。在那里安德列看到有些集体农庄庄员在场上打麦,便扔掉了大衣和帽子,拿起连枷帮着打。追捕的人驰马过去,却没有认出他:他们在匆忙中没有把安德列的‘朋友’带来。
事后他们想起了这一点。他们反绑着‘朋友’的手,一面用刺刀刺他,一面不断地打他的脸颊,踢他的肚子。走过了两三座村庄,德寇在找不到安德列的怒火之下,当街把这位‘朋友’枪毙了。
现在安德列打算上伊雅琴支队去。我想,“他可以给我做个好伙伴。”但是我又高兴幸而没有从干草棚爬下去和他交谈……安德列一定会对我开上一枪的。在他目前的情况之下,他只能这样做。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