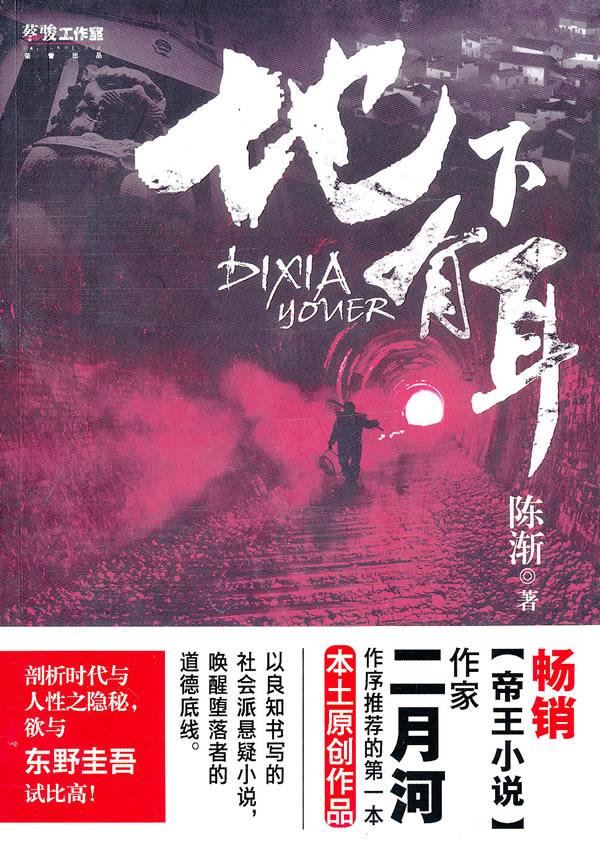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兹命令:
一、本区成立一个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苏维埃积极分子、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统一的游击队。
二、游击队的任务是立即使普列卢基——尼真的铁路丧失运输力,为此必须炸毁加尔卡和普列卢基两站之间的桥梁,炸毁德寇的火车、卡车、仓库;全面展开反抗德国占领者的斗争。
三、为通缉和制裁卖国贼起见,批准一个由斯托拉盛科、普廖德科和普钦科组成的三人非常委员会。
四、批准组织小组,以扑灭曾加入德国法西斯组织的卖国贼。自十一月三日到十日在本区执行,消灭下列卖国贼:
甲:本区伪村长尼依米沙和他的主力雷先柯——处以死刑。
乙:列索沃耶的伪村长兼地主多迈托维奇——处以死刑。
丙:列得科夫卡村的伪村长——处以死刑。
五、为了在本区居民间进行日常的群众政治工作,每村留下共产党员一人和共青团员两人,为了此项目的,应利用留在当地的苏维埃集体农庄的积极分子。
六、任务完成之后,全队于十一月十一日在指定地点集合,以便遵照即将指定的行军路线行动。
七、本命令须通知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游击队战士、各小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八、巴甫洛夫斯基同志负责检查本命令的执行。
指挥切尔尼多夫省游击运动省司令部
司令员费多尔·奥尔洛夫
命令就是命令。它是不必讨论的,是被接受作为行动指导的,但会议还是开下去。我们当然有很多事要谈。本区的共产党员们到底又聚在一起了。他们一度想分散地生活和工作,而现在大家承认本区领导上所采用的战术是错误的了。
“你瞧,我们哪怕此刻,就在这里林务区里被包围的话,”年青的联合收割机手伊尔钦科说,“我们大家也一定可以一起冲出去的,但是象博契科那样单枪匹马呢……”
窗外,雨还是哗哗地下着。我突然听出潺潺的雨声中有某种杂音——仿佛有人在窗口轻轻地挪动。
大家都警惕起来,自然,我立刻想起了“浸礼教徒”。
“喂,干吧!”我命令那个发言人说。
他从衬衫里拔出手枪,冲了出去。
不多一会儿,我们听到这样的谈话:“啊哈,你这个傻瓜,在这儿干嘛?我刚才很可能一枪打死你!”
这是我们的联合收割机手在说话。
“我不过想要听一下。路上一个人也没有。”
原来是我们守卫通向林务区的要冲的一个岗哨,他受不了孤独,而且又想听听正在进行的会议——于是离开了岗位。
岗哨这件事成为我们谈起纪律问题的导火线。
现在我很难想起这次会议的详情细节了。我记得这次会议根本谈不上秩序和宁静。人们时常彼此打断发言,每个人都急于要倾吐自己的心头话。要知道在沦陷的几个月里,人们已经累积了许多问题、许多印象、许多意见和感情,而这样的大集合还是第一次。这次会议不如说是同志们座谈会来得更正确,它开了一整夜。看林人送给我们一桶开水,那些冻僵了的人都喝到了一杯。
顺便说说,我们查明在我们中间没有职业军人,甚至连预备军官也只有三个。其余的都是些担任农村职业的人:拖拉机手呀,联合收割机手呀,耕作队长呀,畜牧家呀,饲马员呀,村苏维埃的书记和主席呀,当然还有些集体农庄的主席。虽然他们大多数都经历过军事集合,可是连步枪都不是人人能好好地运用。
“我们还得学习。而且要记住,我们将来多半要利用缴获来的武器。”
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德寇当局正在登记专家——农学家、财政工作者和机械师们,大概想要在自己的机关里利用他们,许多人将被迫工作。对于这些人,我们该怎样对待呢?”
这个题目引起了热烈的辩论,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坦白地说出来了。这个问题很快就扩大了范围,同志们谈到了苏维埃人民是怎样生活的,侵略者在推行什么样的政策等等。
当然,德寇要竭力设法从各方面渗入人民生活,要建立机关来榨取一切贵重值钱的东西,他们不但简单地拖走,而且还用说服的方式,千方百计地来毒化人们的意识。我们共产党员们已经隐入地下。但是要知道德寇夺去的不过是土地。人民的心、人民的信仰、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觉心,是德寇无法夺取的。人民照旧信任我们共产党员,跟着我们走,等候我们的发言。游击队是我们的地下军,是在敌人后方的军队。留在被敌人夺取的国土上的共产党员们不应该局限于游击事业。我们的责任是观察一切,了解一切。必须到处都有我们的人。为了要有成效地和敌人斗争,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武器。
在和平时代,省委、区委和共产党员的基层组织,是和人民紧密地联系着的,他们领导着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在敌人占领之下,我们共产党员们也必须完全知道在我们活动的区域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样我们才能到处组织反抗德寇的命令、煽动和宣传。德寇要设法调整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运输和交通。这正是我们和平的职业十分有用的所在。医师、药剂师、农学家、拖拉机手、打字员、演员、清洁女工——我们全都需要,我们号召他们全体参加反抗法西斯匪帮、法西斯意识和德寇即将实施的所谓‘新秩序’的斗争。怠工、破坏、偷袭——是被奴役的人民的合理武器。我们不用怀疑:每一个真正的苏维埃人的心里都在愤怒。每一个苏维埃人都想和敌人作斗争。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做到使人民不仅想要斗争,而且能够斗争。我们必须向他们表明,他们并不孤立,有共产党员的强大地下组织存在,它在引导人民走向解放。
这次切尔尼多夫省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的第一次大会到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才结束。大家站起来唱了国际歌。在分别时,我们大家拥抱;有些同志还接了吻。每个人都知道在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没有谈到冒险,谈到死,或者谈到危难。
我们省委小组——德涅普罗夫斯基、朱勃科、娜佳、普列瓦科和我——决定天一亮就动身去找伊雅琴游击队。
在天亮以前,我们才让自己稍稍休息一下,比柳霍夫卡村有一位红军战士的单身妻子把自己的屋子让给我们使用。屋子虽然寒冷,却还干燥。我们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地板上,直到早晨九点钟光景才醒。
我们又开始旅行了。我们的任务是找伊雅琴游击队,它是切尔尼多夫省内跟我们最邻近的、活动着的游击队。
我们看来是这幅模样:四个男子和一个少妇在一条秋天的十分泥泞的道路上走。他们本身也极不好看。男子里头有一个矮胖子,长者短需,手里拿了根棍子,脚上穿着一双特大的、两只都是左脚的短统靴,湿淋淋的,连靴头也扭歪了。他身上穿着粗糙的手纺毛呢短外衣,用一条马肚带束着腰;短外衣的口袋鼓着。他头上戴着一顶厚厚的旧便帽;怀里塞着不知什么东西,因此腹部凸出来一些尖角……在我看来,不难猜到怀里藏的是几颗手榴弹。但真是奇怪,迎面来的人却猜不到。可是也难说,谁知道这些迎面来的人在想些什么呀。这个矮胖子就是我,费多罗夫,那时候叫费多尔·奥尔洛夫,身份证上是阿列克塞·柯斯提拉。
第二个是个高个子、黑头发、身体相当结实的人,穿着海狸大衣、军用长统靴,便帽直拉到前额上。他迈着大步,样子是威风凛凛、皱眉蹙额、甚至怒气冲冲的。走到了或深或宽的水潭边,高个子便停下来,等待矮胖子。矮胖子伏在他背上,高个子一声不响,也不回答自己的担子大打趣,就把矮胖子背到了另一边。这是帕凡尔·华西里耶维奇·德涅普罗夫斯基,化名叫华西里琴科。
第三个是个青年,穿着一件旧的棉外衣、一条马裤、一双棕黄色绞皮长统靴。虽然裤子上溅了泥浆,短外衣上破了几处,而且脸也好久没有刮;但是这个青年却不可思议地保持文雅潇洒,英姿飒爽,象是在闲逛的样子。看来,他棉外衣里面衬着一件钮扣亮晶晶的军装。因为道路大半要穿过树林和灌木从,这位青年常常一会儿走到右边,一会儿走到左边,跑在前头,攀上小山,张望一阵再回到本队:他在判断有没有危险。这位衣衫褴熡的花花公子,便是我们的侦察员和优秀的同志瓦夏·朱勃科。
妇人穿的是黑棉布裙子和皮外衣,头上包着一条红围巾。她有文学作品中早已描绘过的那种妇女代表的模样儿。显然,她费了莫大的劲才获得这样的装束,目的正是为了符合这种人的样子。她是黑黑的,中等身材,二十三四岁年纪,但是因为头发剪平了,身上又穿着那么一套衣服,所以看起来要老一些。她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特征是认真,而认真的主要特征是面面俱到。她手里提着一个雪白的小包裹,白得象上过浆的。她怎样把这个小包裹经常保持得干干净净倒是个秘密。这个小包裹里装些什么,也是个秘密。这位年青的女人热心地保卫着这个秘密,虽说她的同伴谁也不想去深入了解它。她常常和一个同志走开,不是落在这伙人的后面,便是赶在前面,她一面证明着什么,一面表示责难地摇着头。大概因为她不满意那位同志,所以才把自己的观点解释给别人听吧。当前面路上发现有人的时候,这位穿皮外衣的女人便赶过自己的同志们,第一个去迎见那些陌生人。假如那是德寇或者可疑的人,她便把自己的小包裹搭在肩膀上,那是叫我们注意的暗号。这个女人是娜佳,我们忠实的伙伴。
第五个,过去很胖,但现在几乎是皮包骨了,是个金黄色头发、妙趣横生的人。他自己随时准备‘歌唱’,而且发动别人去附和他。他总是插科打 ,逗弄着人家。当然,娜佳是不会赞成这种行为的。他穿了一件灰色长上衣,帆布高统靴。这位是帕凡尔·洛格文诺维奇·普列瓦科。
在旁观者看来,我们这伙人的移动是这样的:绕圈子,走弯路,仍旧回到老地方;它的人员向不同的方向散开,然后再聚拢来……碰见人的时候,他们时而久久地坐下来谈谈,时而突然转过身去快步向后走开,消失在灌木丛或树林里。在走进村庄时,他们先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屋子才敲门,在半夜里蓦地离开茅舍。在白天,他们钻进干草堆或麦杆垛里去睡觉。
这可以说是一种奇怪的、野蛮的生活。我们变得粗鲁、憔悴,脚上磨起了厚厚的硬茧。总之,在这些没有止境的移动中,我们受到了锻炼。谁也没有伤过风,喝过一滴药水或吃过一包药粉,甚至也不感到忧郁。我们习惯在任何环境之下睡觉,醒来时马上神清气爽。
几天以来,朱勃科已经设法通过伊雅琴区的两个共产党员去确定支队的所在地。他们两个都不能肯定地告诉我们什么,虽然花在寻找上的时间并不少。这件事使我沉不住气了。“要是他们在自己的区里还不能做点工作,那还算什么侦察员哪!”他们确切查明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支队还存在,还在活动,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