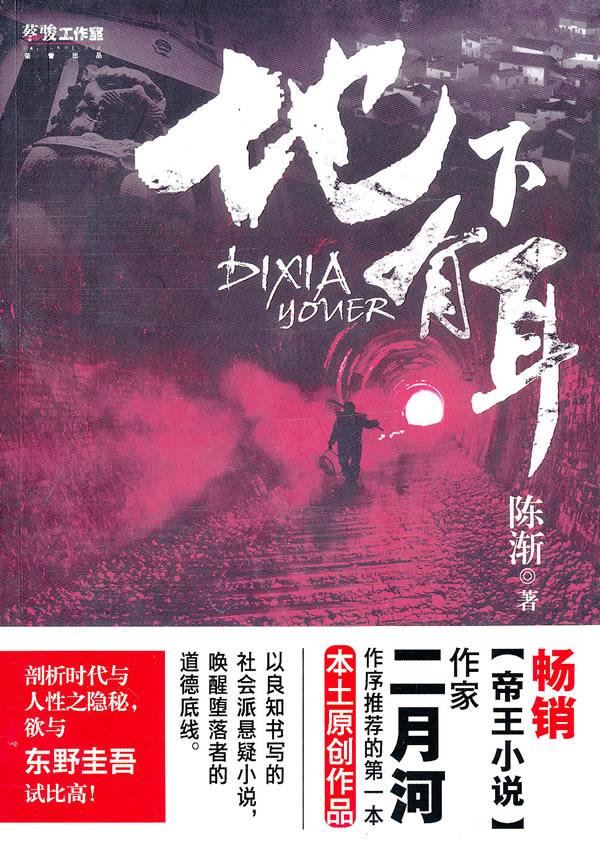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来枪毙我吧……我什么都不知道!”格里沙很勇敢地回答,眼睛里充满了决心。
他的相貌诚实可靠,眼睛炯炯发光——这样的人即使受到枪毙的威胁,也不会吐露一言半语。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他就是游击队员,一个坚强可靠的小伙子。
我凑近他的耳朵低声说:“我是费多罗夫,省委书记,明白吗?我今天一定要和支队指挥员取得联系!”
格里沙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他的脸上掠过一阵笑影,然后带着一种过分的严肃说:“费多罗夫同志,我本人什么都不知道。要是你愿意的话,这里有位集体农庄的会计员斯捷潘·波格列勃诺依,他也许可以告诉您一点儿消息。”
“好,要是你再欺骗我们的话,可当心!……”
当然,他又欺骗了我们。不知是会计员受了他的警告,还是他确实没有在家……
会计员的妻子说:“您可以去找季顿科,他在小学校里开村长会议呢。区长已经到那里召集了各村的村长。”
我勃然大怒了。因为三天来我们已经兜了许多圈子而一无所得。我毕竟不能到街当中去喊:我是费多罗夫,指点指点我到游击队去的路吧!以前,不需要的时候,认得我的人要多少有多少,可是现在呢……难道我真的变了样吗?在战前,我至少到普里蒲特尼来过六次……难道我们真要白跑一场,空手回到彼德罗夫斯克去不成?真的,我甚至惭愧起来。忽然,我想到了一个念头,初看起来似乎又莽撞,又无耻。
“听着,帕凡尔!”我对德涅普罗夫斯基说。“让我们,帕凡尔,让我们到小学校去。不错,不错,到伪村长会议去!应该冒冒险!那里我们一定会碰到一些自己人……况且我们早晚得和区长打打交道,见见这个混蛋。”
德涅普罗夫斯基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顾虑是有理由的:这是一件冒险的事情,要是我们失败了,就可能使全部省组织处在敌人的打击之下。
“您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要是您觉得必要的话……我当然和您一起去。”
我觉得是必要的。我们决定,如果发生什么事故,一定动用手榴弹。弟兄们各人都有五颗。此外,我还有两枝手枪,德涅普罗夫斯基也有一枝。
学校的入口处停了一辆弹簧钢板、橡皮轮胎的马车,套着一对吃得饱饱的、但是身材并不相称的马。这辆老式轿车的座位上铺着大红的沙发坐垫。一个留着胡须的老头儿,身上裹着羊皮袄正坐在车夫座位上打盹儿。这辆车子十之八九是从本区博物馆里没收去的。
“老爹,”我对老头儿说。“村长在这里吗?”
他狡猾地微微一笑,使了个颜色,接着露出令人可笑的、自尊自大的神气说:“小伙子,你说的是哪个村长,这是副区长帕弗洛·格列博维奇·古锡,他亲自视察来了。”
在走廊里,满积尘土的课桌直堆到天花板。教室的门都关着,其中有一间传来了许多说话的声音,我们便敲了门,故作温顺地走了进去,脱下了帽子。
在一张大概原来做物理实验用的大桌子旁边,有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摊在圈椅里捻着胡须。他面貌平庸,可是那套衣服……看来他大概已经穿惯了。他穿的发亮的黑呢上衣,很可能也是博物院里的;还有一件绣花的乌克兰式的衬衣。圈椅子背上披着一件毛皮大衣。我敢断定这个家伙正在扮演老爷的角色——要不是地主,那么无论如何是革命以前的大官。不待说,过了足足有五分钟,他才理会到我们。他那伸出的手里拿着一扎文件,摆在眼前,傲慢地皱着眉毛。
房里还有三个人。一个是浓妆艳抹的胖姑娘,长着一张非常愚蠢的面孔。她显然在扮演女秘书的角色。但是她丝毫没有什么事情做,只是在桌子上描画着花儿。
在这位“要员”后面,靠近窗口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兵。他对我们这边冷冷地瞅了一眼,打个呵欠扭过脸去。他是怎样的角色呢?谁知道他是卫士还是当局的代表?他感到无聊了。
那第四个多半是本地人,红鼻子,从帽檐里搭拉下来的一绺额发,还有那一双醉意朦胧的眼睛,一望而知是个老酒鬼。除了贪杯的欲望以外,在那副尊容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他站在那里,两手支着桌子,显然在听候吩咐。总之,这一切就象一幕极愚蠢的闹剧一样。
这间教室里没有课桌。替代课桌的是中央和靠壁的一排排长凳。在远处的屋角里,生着一个圆形的铁火炉。
我们默默地站着,调换着脚。这些人使我激起了厌恶和痛苦。
终于副区长老爷赏光注意到我们了:“你们要什么?”
我真想抓住他的衣领,拖到街上,在所有真诚老实的老乡们面前揍他一顿,来作为答复。但是我温和地说:
“我们是来找村长的。有一条德国的法律规定,应该帮助所有被释放的战争俘虏。因此我们到村长这里来……”
他浮夸愚蠢,装腔作势,简直是沉醉于自己的地位。他甚至没开口询问我们,也不好好儿看看清楚。他一心一意就是想教训教训人。
“我哪是村长?那才是村长呢,”他指着酒鬼说。“他懂得法律,他什么事都可以给你们做的。”
“嗯,”村长咕噜了一声。
可是这位“老爷”话匣子一开,便关不住了。他不可一世地、指手画脚地说着。
德涅普罗夫斯基问了他几个问题。他说,我们正在慢慢走回老家,却不知道前线情形怎样,也不知道以后怎样生活下去。
“大日尔曼英勇无敌的军队正在扫荡乌拉尔山 的最后一批赤军。莫斯科和彼得堡已经听凭胜利者的摆布。乌克兰已经解救出来了……”这位‘老爷’对自己的口才沾沾自喜,甚至站了起来,昂着头、同时不时回头望望坐在窗口的德国兵。但是那个德国兵却不动声色俱厉地敲着玻璃窗,连连打着呵欠。
老乡们开始聚集起来了。
古锡提议我们两个留下来开会:“来听一下应该怎样建立新生活吧!”
我们当然欣然同意了。我坐在靠近火炉的长凳边上。德涅普罗夫斯基坐在离开我三步的地方。我们才安顿下来,我一瞧,季顿科就进来了。他认识我,一下子弄得茫然无措,面色发白。后来他能自持有了,用相当冷淡的声音问村长这些是什么人。他知道我们是谁以后,就说要在自己的近邻安排我们过夜。
马车不断地向学校驶来。它们从邻村带来了某种类似的“积极分子”。古锡召集来开会的,除了村长和集体农庄主席以外,还有教员、农学家。大多数人都显得十分拘束,谁也不高声说话,连一个面带笑容的人都没有。我还注意到那些人互相避开了别人的注目——似乎感到害臊的样子。是的,大部分人对于答应来听那么一个角色说话,无疑是感到羞愧的。
这时发生了一幕不象样子的情景。另一辆大车驶到校舍来了,我们听到响亮的咒骂声,接着开始了骚动和扭打。
“哎呦!”有人含含糊糊地叫着。“噢,别打啦,好人!”
走廊里又闹了好一阵,接着房门大开——几个怒形于色的农民把一个捆绑着的人用力推进房来。
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壮汉。他象牛一样低着头站在那里,眼睛盯着地板;两只手被一条皮带反绑在背后,扎得发青;蓬乱的头发覆盖着前额;鲜血从嘴角上直流下来。他那肿胀的面颊上显出了一个鞋跟的印子。
古锡扮起了命令式的嘴脸:“噢,这是怎么回事?”
绑着的人向古锡冲过去,古锡双手掩住了脸,好象等着打击似的。
“啊,你这个畜生!”押着进来的农民中的一个喊着,一拳把他打得跪了下来。另一个农民冲上去,踢他的侧腰;一个手里拿着包袱的老大娘几次三番地向他脸上吐唾沫。总之,我们弄得莫名其妙。
当怒火稍稍平息下来,绑着的人给拖到了屋角里去的时候,古锡声音中含着希望问:“他是什么人,是游击队员吗?”
大家抢着想回答,又引起了一阵喧哗。古锡嫌恶地紧闭着嘴唇。过了十分钟光景,才算把这件事弄明白。
在红军撤退以后,有个绰号叫“野猪”的斯皮里顿·维丘克回到了格卢霍夫申农庄。他已经长远不在故乡的村子里出现,大概有八年了吧。他是个有名的废物——扒手、土匪,因为在伏罗希洛夫格勒抢劫一家洗衣铺,被判处了七年徒刑,在某地劳改营里服役。‘野猪’在农庄一出现,首先就搞了一部做土烧酒的器具。他不断地喝酒,而且扬言要出头告发来威胁大家。昨天夜里,人们听到林边木房子里有叫喊声,红军军官的妻子玛丽娅·卡柳什娜娅就住在那里。赶到现场的农民们迎面碰见她背上插了一把刀子从屋里冲出来,倒地就死了。他们在屋子里,还发现她七岁的女儿娜丝佳被绞死了,她三岁的儿子瓦夏受了重伤,并且给嚇坏了。
农民们急忙去搜索森林,‘野猪’就在那里给抓住了。
古锡开始审问他。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就连那个德国兵也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嘴。
接着‘野猪’走到古锡身边,低声说了几句。
古锡立刻跳起来对着讲堂喊道:“这里有德文教员吗?我们需要一位翻译。”
一个老大娘站了起来。古锡让她在德国兵旁边坐下。
“好,你有什么话说?”古锡故作严厉地问。
这个土匪向古锡拿头点了一下自己上衣的口袋。古锡伸手进‘野猪’的口袋里,取出一张揉皱了的文件,细看了好一会,然后转交给德国兵。德国兵点了点头就把文件还给了他。
“好,”古锡说,“好,好,”他紧皱着眉头反复说。他显然不知怎么办才好。‘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公民叫维丘克,是德军司令部的特派员。”古锡转脸对绑着的人说:“这是个误会,立刻给您松绑。”
土匪站了起来,无耻地向全场的人扫了一眼:“区长老爷,”他高声说,“我注意到:玛丽娅·卡柳什娜娅和游击队员有往来。她丈夫是共产党员。区长老爷,全农庄的人都是游击队员!”
“胡说,他在胡说八道!”庄员们齐声叫喊着。
讲堂里传播着不安的情绪。大家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有人喊道:“吊死这个凶手!”
一直留神监视大家的德国兵跳了起来,对着天花板开放德国式连放手枪,一刹那间房里变得寂静无声。
德国人重新坐下,扯了扯翻译员的袖子。
“我是个警察,”维丘克反驳说。“游击队员们每天去找玛丽亚·卡柳什娜亚……”
“你既然要整顿秩序,为什么要抢这个东西呢!?”老大娘说着这句话,把一个大包袱扔在桌子上。
“这是没收来的东西。”土匪毫不惭愧地说。
“没收”这个词儿对德国兵起了魔法的作用。他激动了,尽催着翻译员。
她站起来用断断续续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德国老总说,要提醒您,副区长老爷,按照现行的指令,一切由市政当局没收的贵重金属品,还有宝石、油画与雕刻的美术品,都应当转交给‘戈林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