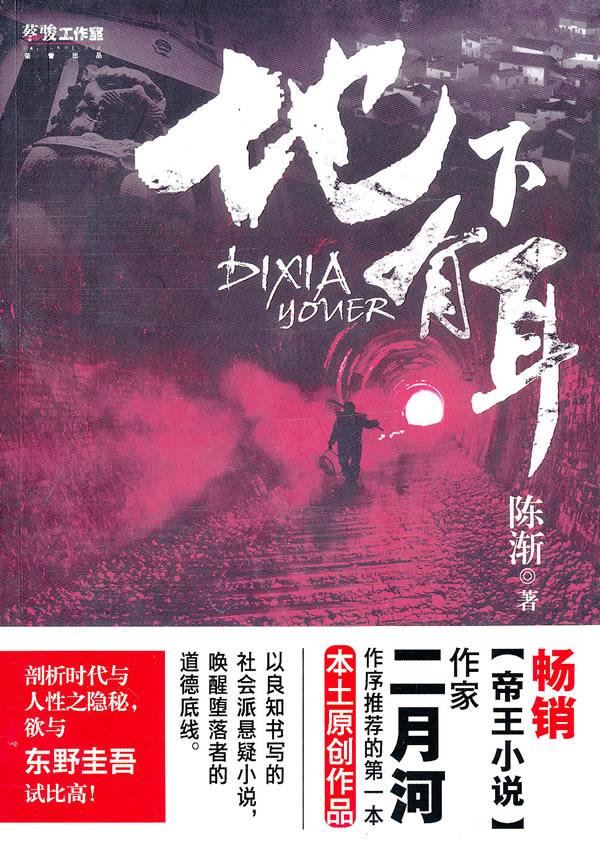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了消除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奴仆们的掠夺行为,我命令:
一、严禁全体公民交出勒索品——粮食、牲畜、马铃薯及其他产品给德国占领者。
二、凡违犯本命令,解送粮食、牲畜、马铃薯及其他产品给德国法西斯占领军者,应视为苏维埃祖国的卑鄙无耻的叛徒,将受革命政权的严厉制裁。
三、游击队指挥员应在向各地运送产品的路上派出秘密哨兵。
四、凡执行德寇命令运送勒索品的伪村长和伪警,应立即连同他们的蛇窟一并予以消灭。
男女农民同志们!不让一公斤的粮食、肉品、马铃薯和其他产品留给德国法西斯强盗!
女主人找不到钉子,也没有浆糊。娜佳看到窗台上有一盒留声机唱针,我们决定利用它。
一吃过晚饭,朱勃科和普列瓦科便跟着当向导的女主人出发了;他们把德寇张贴的布告都撕下,而在原处钉上我们的命令。
女主人把我们安置得都很舒服。给风湿症折磨着的德涅普罗夫斯基爬上了炉台。我们睡得好极了。
女主人在天亮时叫醒了我们。原来她丈夫回来说……伏洛费察村已一个德军都不剩——全都逃跑了。
老实说,当我们草拟命令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有这样的效果。我们只想表明游击队并不在打磕睡。这是个出乎意外的结果。这意味着在苏维埃国土上,敌人感到毫无把握。
的确,主人已告诉我们,粮食收集部队是由一个瘦弱而胆小的军需官带领的。他一接到“命令”的通知,便慌慌张张东奔西跑,并且说侦察兵早已对他报告:大批游击队已经逼近了。
我们大家吃了一顿精美的早餐之后,主人便引导我们到捷斯那河边,并且把一处狭窄而冻得挺坚实的渡口指给我们。他还给我们指点了到霍尔梅区的列依明塔罗夫卡村取得捷径。
“同志们,再见!”他分别时说,“列依明塔罗夫卡村有人知道米谷拉·纳普德连柯的……”附近各村的许多农民不知怎的都这样念歪了尼古拉依·尼基吉奇的名字。
我把伏洛费察的主人们的名字忘了,真是可惜。他们夫妇俩毫无疑问都是极好的苏维埃人。
在捷斯那河边,我们得和冲锋枪手们分手了;从这里起,展开了一片相当茂密的树林,躲起来是很容易的,我们没有他们也行。正要分手的时候,有一名冲锋枪手忽然说,他想要单独和我谈谈。
我们走到一边矮林里去。这位同志没有马上开口说话,使我有时间来更仔细地把他看个清楚。老实说,虽然我们已经相处了大约三昼夜,也交谈过,我却没有对任何一个向导加以特别注意。这两名战士——游击队员——一个比较年青行,另一个年长些。现在我好奇起来了,仔细地打量着他。
我面前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高个子,穿着一件按城市式样缝制的厚呢大衣,鼻梁上有夹鼻镜的印子。我想起了一路上他常常把冲锋枪从这肩换到那肩。从这一切可以断定他是个城里人,一个脑力劳动者。我想:“嗯,他要抱怨支队的领导了。”
“费多罗夫同志,”他开始有点犹豫不定,但很严正地说,“我向您最高苏维埃代表兼政府委员请示。问题在于我可能被打死……”
“被谁打死?为什么?”
“我想是被德寇或者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总之,您要知道,这是战争啊。”
“是的,这当然是可能发生的,”我不得不同意说。“只是请您扼要地说吧。您瞧,我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地方可以关起门来谈谈。坦白地说出您的秘密吧。”
这时他急急忙忙解开大衣,翻开大衣前襟,用手指撕开点儿衬里,抽出了一个扁扁的容积相当大的包儿。
他一面说,一面把包儿递给我:“瞧,这里一共是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三卢布。这笔款子是属于肉类牛奶工业人民委员会木材采购办事处的,是基辅撤退那天保管在握手里的现金。我是会计主任,我的名字是……”
我当时就记下了这位同志的名字,但此后那张字条就失落了——在三年的游击生涯中,这是不足为奇的。
会计员把名字告诉我以后,接着说:“我是和一小组同事一起撤退的,我们的火车在路上被德寇炸坏了,后来我陷入包围,后来……在来到支队以前,我吃尽了千辛万苦。我恳求您收下了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实在无力保管它。这是国家的钱,我不仅没有保险柜,甚至连一只手提箱也没有,此外,我可能被杀死……”
“但是您为什么不把这笔钱交给支队指挥员呢?万一您阵亡了,或者甚至挂了彩色,同志们会翻看您的东西……会误认你是个抢劫犯或者……”
“问题就在这里!但我不能把这笔钱交给指挥员,费多罗夫同志。这必须在现金转帐表上签字,而他没有这种权力……”
“听着,会计员同志,我只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把这一切保守秘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您该当着几位证人的面……”
“不,您知道,这是一笔巨款,人又是不认识,局势又是这样。”
“好,让我们来看看转帐表吧,在哪里签字呢?”
“就在这里,不过请您点点数。”
“为什么?要知道我反正立刻要把它烧掉的。”
“但是必须点点数,费多罗夫同志。您无权信任我。”
“我完全信任您。我们把武器和保卫人民的任务都托付给您了。我看得出您是个老实人,为什么要耗费一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来点这些钞票呢?”
“费多罗夫同志!”会计员喊道,声音中流露出了愤激。“我懂得,但是不能不这么办。我已经当出纳员和会计员管理银钱三十二年了……”
我耸了耸肩膀,叹了口气,便动手钞票。不待说,一个戈比都不差。
叫旁人看来,我们的样子显然是很古怪的。在水流冰结的河岸上,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坐在撒着雪花的矮树林下面点钞票。
接着我们把钞票烧了,我便在这独特的篝火上烤着手指:点钞票的时候,我手指都冻僵了。
等候我们的同志们,也冷得直打冷战。朱勃科和普列瓦科抖得特别厉害。他们因为我的长久不在场而弄得坐立不安,就紧贴着冰冷的地面爬到会计员和我藏身的地方。
“您好久不回来,我们以为……但是看到您在点钞票时……我们才放了心。”普列瓦科说。
会计员对他惊奇地瞅了一眼,显然很难理解为什么竟能对金钱漠不关心。在道别时,他长久地握着我的手:“谢谢您,费多罗夫同志!现在我会觉得轻松些,仗也会打得更好了,不会那么害怕被打死了。”
我们早在伊琴雅支队时就打听到波布特连科和他的部下已科留可夫卡区转移到霍尔梅区。因此我们便往列依明塔罗夫卡——一个坐落在大森林边沿上的村庄去了。毫无疑问,这个村子里有一些和省支队保持联系的人。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懂得要找到游击队也不那么容易。
我们在伊琴雅支队里休息了一下,换过衣服,现在觉得更强健了。令人爽快的天气已经来到:不太冷,间或飘些雪花——是十一月中旬的天气。我们走起路来很轻快,两脚不再陷进泥泞里去了。我发觉同志们变得更沉默寡言了。我们大家在考虑一些问题。
我已经在德寇占领区里两个月了。祖国发生了些什么事,战争进行得怎样啦?
在这个这段时间里,我只听过两次无线电广播:一次在戈洛波罗特科家,一次在伊琴雅支队里。我贪婪地听着,竭力想根据两三次苏联情报部通报的片段新闻,想象战争的全部过程。战争在莫斯科的外围进行;我们的首都,我们祖国的心脏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也许,这种消息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象在沦陷区里使人感到这样沉重痛苦的心情吧。
红军的指挥员们,我们苏维埃后方生产部门的工人们和领导人员们,自由苏维埃国土上的集体农庄庄员们-都有具体、清楚、正确规定的工作。可是我们地下工作者却刚刚在摸索道路,摸索组织的形式,刚刚在聚集力量和武器。
在这两个月里,我看见了些什么,又学到了些什么呢?
我见过很多,会过好几百人,和几十个各种不同的人谈过话。
于是我开始总结,开始综合观察;开始评定会晤、谈话和思想;开始找主要的和典型的事情。要知道不这么做,我们决不能求得地下工作和游击斗争的正确战术。
在记忆中保留的那些清洁,我已经写下来了。自然,那时我记得更多,一切事情都接近些,清楚些。但是主要的情节就是这些。
顺便提一句,我不能抱怨自己的记忆力。它保留了最重要、最典型的事实和观察的印象。
例如:在德寇占领切尔尼多夫的不久以前,我和一批未来的地下工作者一起参加了敷雷课程的研究班,有一次上课时,我口袋里放着一些易燃火柴。我无意地拍了一下口袋,火柴便猛得烧起来,把我的腿烧伤得很厉害,当然,这是我很难忘记的一件事。然而当我写到在切尔尼多夫的最后几天的居留时,这件意外的事情到底没有想起。
可是这里还有另一件小事,我倒记得详详细细,清清楚楚。这是在彼德罗夫斯克农庄,有一回我坐在茅舍的台阶上。两个不知怎的焦急不安的妇人走来看我。
“您也许是党员吧?”她们中的一个问。
我回答说不是。两个人都失望了。这时我就问起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们勉强告诉我说,是因为争执一只小猪。好象是玛露霞从彼拉格依那里把猪偷走了。可是玛露霞坚持说,这只小猪还只有一点儿大的时候,彼拉格依的儿子便在她姐姐那里把它偷去了。
我莫名其妙地问这两位吵架的人:“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找共产党员呢?”
“我们不请教党员请教谁呢?这会儿没有法院,也没有民警。区里有村长,有警察局,但是这种法官难道可以算得法官吗?!”
我刚才说过的那位会计员要把钱交给我,并不是因为费多罗夫引起他个人的偏爱,而是因为我是代表——人民的受托人。
于是我回想到这两个爱吵架的人的事情,与其说是因为这件事滑稽可笑,不如说是因为它说明了人民对共产党员的态度。
在博罗克村里,有人对我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德寇在大路上抓住了一批人。这不是一个组织起来的小组,不过是些同路人罢了。他们都想穿进游击队据有的森林里去,萍水相逢,彼此并不了解。这个小组里有两个是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都是党员;有一个是集体农庄的主席——他烧掉了粮食仓库和成垛的庄稼,然后正确地决定,最好还是离开自己的村子;还有一个共青团区委的指导员;最后加入这个组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叔叔,是附近村子里的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点也不了解他。
这组里的三个人——集体农庄主席、区委指导员和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都有粗枝大叶的毛病,竟把自己的身份证带在身上。由集中营里逃出来的另一个人虽然拆下了军大衣上的中尉领章,但是领章的模糊的痕迹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