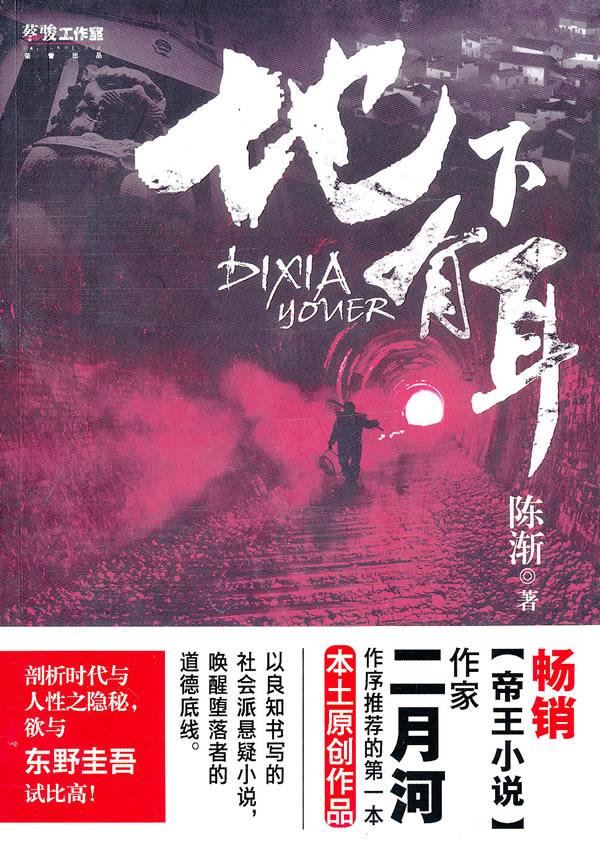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省委谴责了推举指挥员职位的实行人,并且要求驻扎在切尔尼多夫省地区的所有支队应和省司令部保持联系,以自己的行动来配合他。
同时省委进行了巩固单一指挥制和司令员的权威的工作。司令员的决定就是法律。省委要求立即制止任何想开会讨论关于已经采取的决议、想讨论司令员的命令的企图。
游击队员是沦陷区的自由公民。但这并不是在树林里散步的自由。决不能把个人的自由和全体苏维埃人民的自由分开。现代战争中的游击队员必须把自己看作是红军战士一样。我们对每一个游击队员说:
“你来参军是因为苏维埃国家的宪法责成你担负起这种义务。亲爱的同志,你不要忘记,虽然敌人已经来到这里,但乌克兰依旧是伟大苏联的一部分。你参加游击队是因为苏维埃公民的良心使你承担这种义务。因此你得衷心地、自觉地遵守纪律。你自愿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推卸不遵守纪律的责任。”
有些同志对这种立场很惊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穿制服,我们的人员如象平民一样。在我们中间甚至有不应该担当军役义务的。例如老年人或是妇女,还有些几乎是小孩子的少年人。原来,他们也应该服从军纪吗?
有人报告我,一位自由行动的热烈拥护这鼓吹着这样的见解:
“在红军撤退的时候,也许,我便存心留在这儿树林里。”他说,“我热爱游击主义,这就是说要自由——没有别的!你是个司令员,这意味着什么呢?司令员就是人们跟着他奋起打仗的人!游击队员是不能压制的。游击队员就象森林里的野兽、象只狼,必须打击敌人的时候,便聚成一群;打完了仗,又是自己的主人!”
我把这只“狼”叫到司令部来了。
“那么你认真说,你留在森林里是所谓自动精神,是真的吗?”
“我是切尔尼多夫本地人,”他回答道,“我不想远离切尔尼多夫。我打定主意只在本乡的土地上复仇和作战。”
“你所谓‘不想’是什么意思?原来你是从军队里开小差出来的,是不是?”
“我依自己的性格,认为当游击队员格外有用。军纪压制了我的个性。”
“不,请你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从红军里开小差出来的?”
“个人自由”的拥护者有些懊丧了。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四周望望,看到得不着司令部里任何人的支持。
“我没有开小差,只是换了个兵种罢了。”他答道。
“你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吗?”
“我良心下的命令。”
“如果你的良心把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也取消了,那请问你的良心是几级的?把武器缴下,到禁闭所去!”
我必须说,幸而这个“狼的自由”的爱好者后来完全改变了,而且,仗也打得挺好。
省委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培养游击队员对红军的敬爱。我们每个人原都高兴成为红军的战士或军官。我们必须明白,游击运动是红军暂时失利的结果,是敌军暂时优势的结果,是我们被迫在自己领土上作战的结果。当红军在我们的协助之下从这里打走敌人的时候,我们将因加入它的行列而自豪和高兴。
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同志,是从军队里跑到游击队来的。他懂得什么是军纪。我们只要提醒他不应该放肆任性就行。可是,大部分游击队员,特别是在初期,全是公民、全是彻头彻尾的普通人组成的,要他们坚决放弃批评和讨论的习惯是困难的,要他们改变战前对自身的想法也是困难的。
有一回我查明,有些战士正用尽一切正当或不正当的方法逃避执行哨兵勤务和经济勤务。有人报告我,有一个十分令人敬爱的人连一次岗都没有值过。
“不错,这是事实。”那位同志承认了。“但本来是他们请求我的:‘喂,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让我们来替你值夜吧。你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受不了……’”
“这些人多么高尚啊!”
“不错,他们确实是高尚的。但是这些鬼家伙行这种好事讨价却很高。”
“多少?这几天是怎样的定价?”
“这得看什么事情。瞧,比如说,倘使在粮食仓库值一次班,是一把黄花烟或者两大片面包;要是在厨房里削马铃薯,代价就要小些。”
“难道人们的面包不够吃吗?你往那里去拿多余的面包呢?”
“不错,你要知道,就我个人来说是足够了。我是在这儿游击队里才开始抽烟的。抽得不多,而且吃得也不多……”
“自然,你既然工作做得少,吃也就吃得少了。”
“这只有一部分对。不过需要面包的,主要是那些受过包围的或是脱逃的战俘的新队员。他们在森林里流浪的时候,饿够了……噢,这些人简直可怜。老实话,这是他们自己要求的。”
当这位同志挨了骂、受了处分的时候,他抱怨了。
我不打算引证所有违反纪律的事件,虽然这些事件并不太多。可是,那时我们的人数也不多。这些人也都很好,大家都是自愿来的,并且大多数游击队员是在德寇入侵以前报名入队的。就拿这一点来讲,便表明这些人是诚心诚意来打仗的。我们省支队的人员大都是产业工人,党、团的工作人员,是一些最忠实与苏维埃的制度的人。后来支队又补充了很多人,其中有些不能自夸问心无愧的人。他们应该拿自己的鲜血来洗掉自己对祖国的罪过。
在那段组织时期中,我们的毛病,我可以说,是一种成长过程中的毛病。这些毛病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对战争期限的观念极端模糊,并且脱离群众。是的,我们毫无疑义是脱离群众的。支队已经在森林里呆了大约三个月,游击队员们却很少和居民来往,不论是沦陷区城乡居民的生活或是利益,他们都知道得很少。
脱离群众,脱离人民,能使我们遭致灭亡。省委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使人们把游击斗争看作是长时期的斗争。红军转入攻势和肃清本省的德寇愈快愈好。暂时应该停止关于战事期限的谈话,不去难过,不去想到怎样坚持下去,而要行动起来。
省委给了司令部一个指示:准备大规模的进攻战。这次进攻战应该成为我们的人员、我们的组织的全部质量的考验。
按照省委会的任务,我们派了一小组同志在萨凡基村。这个小组必须一方面执行省委的决议,一方面同居民们发生联系,进行鼓动群众的工作。
我也去了。这是我在沦陷的情况下初次参加的农民集会。也许因此我才记得这么清楚吧。后来我常常有机会出席类似的农民集会作报告;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一切算是新的。
我的同伴们也对我说过,他们有一种半信半疑,甚至忐忑不安的古怪感觉。危险吗?不是,我们知道附近没有大股敌军。情况已经预先侦察过了。我们的人员——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和萨凡基的积极分子——曾经事先通知老乡们四面布置了步哨。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焦急不安。
自然,使我们不安的,是情况的特殊和新奇。他们会怎样接待我们呢?怎样举行这种集会呢?就是组织上的一些问题也不清楚。比方说,该不该使这样的集会隆重举行呢?要不要主席团呢?我们中间有些人主张隆重一点,说这是加强印象。
更重要的是应该正确地规定主要日程。在战前,每一次会议都是来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的。讨论集体农庄的生产计划呀;总结工作队和工作组之间的社会主义竞赛呀,集体农庄管理部的报告呀,承购公债呀……议事日程,多得很,甚至如果到了一位作国际局势报告的演讲人,集体农庄庄员们也预先知道演讲的内容,准备一些问题。
而我们这次来,可以说是为了进行一般的访问:大家认识一下,交换些消息,了解一下老乡们的心情。不待说,那天的一些主要问题是对侵略者的不共戴天的斗争和支援游击运动。但是我们还不能对萨凡基的集体农庄庄员们提出具体的作战计划。
我们骑马到了一所小学校。大厅里已经摆好一张桌子,桌上铺着红台布,桌子上方挂着一幅斯大林的画像。两盏油灯暗淡地照着屋子。组织者们尽赔不是:“到处找不到火油,只得把牛油加在油灯里了。”
人们没有一下子集合,三三两两地走进来。有些人认为必须装作看见灯光偶然走进来的。相反地,另一些人却带着故意引人注目的决心走了进来:坚定地迈着步子,直望着前方,不必要地高声说着话。
姑娘们和大娘们在入口处 不前地站了好一阵,叽叽咕咕,偷眼往里瞧。叫她们进来,她们却回绝了。到后来,会开得正紧张时,她们才完全悄悄地走了进来。
我们的政委雅列明科讲话了:“现在我请游击队司令员兼地下省委书记讲话……因为秘密活动的缘故,我不讲出名字了,换句话说,这是机密……”
我站了起来,想开始讲话,但是大厅里却不知怎的发出了哧哧一笑,接着又是一声。有些人简直放声大笑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干么呀?
“啊,原来是费多罗夫!”
“对,正是费多罗夫。”
“这是什么秘密呀?这是费多罗夫!”有人在后排喊了一声。
雅列明科皱着眉头,我却笑出了声,而且顿时对这些人发生了亲切温暖之感。也许正因为是在此时、此地吧,可是我不知怎的一下子就变得平凡而真诚了。
我简要地说明了游击队员是些什么人,他们怎样作战,为什么作战。我传达了最近的苏联情报部通报的内容。他们十分出神地听着。
我一讲完,雅列明科便向出席的人们问道:“有问题吗?”
第一个喊了一声的是一个坐在远远的角落里的年青小伙子:“费多罗夫同志,请您告诉我,您是怎样独自去参加普里蒲特尼的伪村长会议的?”
“但是,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两个……你从谁那里听来的?”
“这件事不仅我一个人知道。人们都在兴高采烈地谈着呢。听说您把伪市长本人和五个伪警都打死了。”
关于游击队功绩的故事,在居民们中间传播得惊人的迅速。正如读者已经知道的,普里蒲特尼村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件小小的事情传开了,人们的传说给夸大了。
“不,”我说。“我们先不谈这些。”
立刻就有好几个人支持我的意见:“难道费多罗夫同志是个演员,一定要讲给你听吗?”
“咱们不是到这里来聊天!”
“最好你讲一讲,你为什么不参加游击队……”
小伙子们开始“嘘”了。
他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然后大家开始提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重大的,我回答起来都感到吃力。有许多问题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些问题里包含了农民的一切期望和思想,而且提出来的时候是自然而然、诚心诚意的。我懂得他们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党提出的。
一个高高的、外貌阴郁的、上了年纪的农民,这样说道:“费多罗夫同志,共产党对于其他的强国是怎样想法的?比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