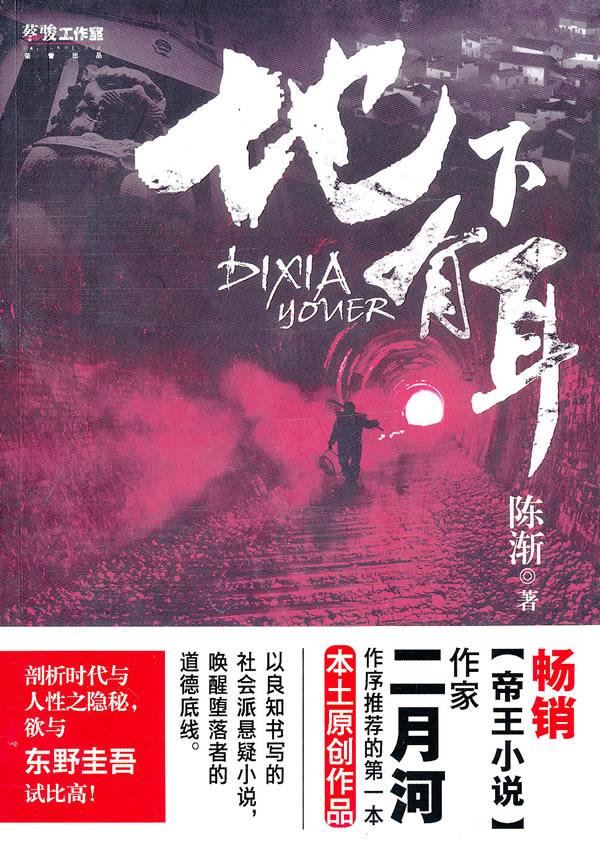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在树林边上的灌木从里看见了三个红军战士。他们的肩上全都挂着一支装得胀鼓鼓的大背包。他们服装不整,大衣虽然肮脏,却是完整的,长统靴看来也很结实。
这三个人看来全是汽车驾驶员。他们简短地讲了一遍自己被围的经过。我自称为团政委。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相信我,或是反正他们对这些不管,但他们收容了我,“还给了我给养。”
“政治委员,我们大家来商量商量,”他们中的一个说,这人生得满脸横肉,目光险恶。
他这样说了以后,对他的朋友们使了个颜色。我跟着他们向一个大干草堆走去。有人已经在草堆里面掘了一个宽大的坑儿,有点象窖洞的样子。我们爬了进去,觉得很舒适。
那个目光险恶的驾驶员解开了背包,拿出两个罐头,一壶军用水壶伏特加酒和一大块面包。他从容不迫地把面包切开,再用一个灵巧的动作打开了罐头,把肉分放在一块块面包上,又在空罐里倒了些酒,然后把第一个递给我。
接着大家轮流着喝。我们开始吃起来。一个头发漆黑、活泼机警、看来象是犹太人的驾驶员,对那个险恶的伙伴说:“喂,斯捷潘,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躲在这堆干草里吗?”
斯捷潘朝他很快地扫了一眼,什么也没有说。
第三个驾驶员是一个脸上有麻点的小伙子,说话带着维雅特卡口音,他在险恶的斯捷潘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说:“斯捷潘,让咱们设法钻过前线,到自己人那里去吧。现在我们有位政委在一起,从各方面看来,他是个强壮的庄稼汉,我们带他一起走。”
现在斯捷潘的目光注视着我,把一只多毛的长手伸到我胸前的勋章上,碰了一下说:“是呀,我们正差这么一位政委,”看来他马上就醉了。“噢,傻瓜,别着那个玩意儿干什么呀?”他瞪着勋章说。“拿下,要不,我来拿!”
“去,别动,”麻子说。“别找麻烦,斯捷潘,让咱们来谈谈正经事。”
“正经事?什么正经事?我们的正经事是喝酒!”斯捷潘喃喃地说。他又给自己倒了些酒,喝完了,拿手掌抹了抹嘴,继续那么不慌不忙地说:“我们的正经事很简单:我们搀着政委的手,带到最近的村庄的司令官那里去,让那边来审判谁该送集中营,谁该上绞架。我们带了这位政委去,德国人就会更信任我们!”
一发觉我伸手到怀里去,他就抓住我的手。“慢着,老兄,别恐嚇,我们来得及打的。你这个玩意儿我也有的……把你的勋章扔在干草里吧。这就是你的证件。”
说着这些话,他从口袋里抽出几张德寇的传单——“通行证。”
我使劲从他强有力的手指中挣开手来,拔出了手枪……坐在我右边的麻子猛地一下子把手枪从我手里敲落了。我想要扑住他,可是他已经一个虎跳跳在斯捷潘身上。
“混蛋,想出卖吗!……”
黑头发的也冲到他身边去帮忙,他们俩把自己的伙伴按在地上。
“等一下,弟兄们,好兄弟!”斯捷潘叫着。他一面拳打脚踢抵抗,一面乱咬,但突然不知怎的不自然地气喘呼呼起来,开始拿脚后跟槌地了。
不一会儿,一切都结束了。
我爬到外面来,在新鲜的空气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黑头发的和麻子马上拖着自己的背包跟着我爬了出来。
麻子眼睛望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狗只配狗的死法!”
他拿手抹去了脸上的汗,对我说:“政委同志,为什么要白白地开枪呢,搞得挺吵闹的。有时侯悄悄地干好……”
我们不再提起这件事,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一起走进了森林的深处,我是在想这两名红军战士教导我的果断精神和必要的残忍。
黑发人的背包里找出了一件雨衣。这件雨衣又短又旧,但是我穿在身上感到很适意。它勉强挡得住风吹雨打。他们又给了我一顶破破烂烂的船形帽。现在我真的象一个脱逃的战俘了。
我发觉我们马上就要分手了。麻脸小伙子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越过战线去。他在找同伴。我到切尔尼多夫省去的企图没有改变。他们叫他雅可夫·祖谢尔门的那个黑发人,一心一意想回到故乡尼真市去。这个城市也在切尔尼多夫省里,所以我到这时还是和雅可夫同路。
树林里有许多人在流浪。想必,大多数也是象我们一样的流浪人。
常常有这样的事:一个什么人走来了,显然是看见了我们,便向我们走来。我们一喊他:“朋友,我们是自己人,到这里来!”
但是他却会突然拐到一边跑起来了。单身汉尤其害怕。这是可以理解的:谁知道那是些什么人呀……
我们在草料场的干草堆里过夜了。大家轮流睡觉。第二天早晨,我很高兴地发现:我的脚已经好一些了。
吃了一点东西,我们就毅然决定:一定要百折不回地去找些人来集成一队,不一定要是游击队员,哪怕是志同道合的人也好。人越多,力量就越大。
我们正在商量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男小孩在不远的地方跑来跑去。我们叫住了他。他相当勇敢地走了过来。
“小伙子,这里看见过游击队吗?”
“什……什么是游击队啊?”
小孩子耍滑头了。顺便说说,他肩上挂着两只很大的军用短统靴。
“哪儿拿来的?”麻子问道。“送给我们的司令员吧,你瞧,他没有鞋子穿。”
孩子毫不吝惜地把短统靴从肩上拿下来。这两支靴子都是左脚穿的,但都穿得进。因为靴子十分宽大,我仍把大衣的破片裹在脚上。
我谢了谢孩子,就问:“噢,你当真没见过游击队吗?”
“就在那边,在洼地那边有些叔叔,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走这条路过去。”他给我们指点了方向,我们便动身了。
现在我觉得仿佛成了国王的教父。我的两只脚暖和了。凡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这是何等重要的。不错,我时常绊倒,但仍是兴高采烈。
当我在洼地那边的一伙人里面找到了熟人——两天前失散的我们小队里的两名红军战士时,我分外快乐了。
他们告诉我,在那晚的遭遇战中,六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受伤被俘。其余的人都脱身了。他们以为我已经牺牲。中尉早上带了一名战士出去侦察,也没有回来……
我们一共七个人,在洼地旁边围着篝火坐下来。其中两个决意要到基辅和日托米尔省的故乡去,其余的人都一定要越过前线。操维雅特卡口音的驾驶员参加了我们这一批。
在篝火旁的这个小组里头,彼此谁也没有好好地了解,大家的心情自然根本是不愉快的。但是围着篝火的俄罗斯人能够保持沉默吗?所以我们也谈天了。
“嗳,我们这个国家是伟大的。”一个穿着军大衣的高个子年青人说。他仰面躺着,凝视着天空。“我们的国家会支持得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
这个问题是什么,他可没有说出来。
其实,我们的谈话也不外是这些不确定的感叹和批评。我们时时停下来倾听远处的枪声和树叶的沙沙声。我们也互相提防;我常常抓住对我留心估量的眼光。
“糟透了!”一个短小的红军战士喊了一声,他腰间的皮带束得紧得不能再紧。“华斯卡·谢迪克给一块弹片砍死了,我倒逃过了,有机会活下来……弟兄们,我们不在军队里还成什么人?单个儿来讲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都能唱祖国进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但是剩下你一个人,你就光想吃。”
“这就得看是什么人,”望着天空的年青人反驳道,他已经忍耐不住,站起身来了。“干么你唠唠叨叨,没完没结?你对国家和祖国懂得些什么?我要好好地揍你一下……清醒清醒你的脑子!”他开始卷纸烟,显然打算聚精会神地想一下。“瞧,我正躺在这里想,你说,我想的是什么?”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短小的红军战士回答道。“你在想老婆、想孩子、想自己的可恶的境遇,还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吃午饭。”
“你真是个傻瓜。瞧,我们这里一共十个人。如果你请教每一个人,你就会知道,他并不在想自己的物质需要,正相反,把它们撂在一边。我现在想的是乌拉尔的机器厂,我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那里有这么一个工厂:那里能出产多少坦克……那末你在想什么呢?”他突然问起右边的邻人。
那个人脱了靴子坐在那里,在火上烘着那正在化脓的大脚趾。这个人脸色苍白,显得十分疲倦,眼睛也困乏地失去了神采。
“你说我吗?我不在想什么,敬爱的同志。我在幻想。一般说来,我是个理想家。我想怎样使这个德国走上正路,因为他们-我是指德国人——现在只干消灭人类的勾当。等我这支脚好些,马马虎虎能把这支长统靴穿上,把步枪挂上肩膀——我便出发。不管要走多少路,不管要转多少弯,我一定要走到柏林!当我们卡住希特勒的喉咙时,才可以解释……”他咳嗽起来,显然是累得连说话也感到困难了。
“朋友,你呀,在到达柏林之前,会死上七次!”短小的红军战士对他高声说。
“至于说死,我不愿意平平常常地死,我可能会在战斗中牺牲。可是即使在我战死的前夜,我仍将幻想和计划……”
虽然他用低低的、平静的声音说这几句话,他脸上却有一种不由你不相信的信心。
“对,朋友,说得对!”从篝火另一边,有一个人在兴高采烈地叫着,他满脸儿闪闪发光。“我们,象你我这样的人们,我意思是说苏维埃人民,没有对将来的理想就没有生活。我是一个技师,过去在德涅泊尔水力发电站工作。早在修建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学习了。现在这个晚上我盖着树叶睡在地上,一面冻得牙齿格格作响,一面在想,一旦德寇给赶走以后,我们将怎样着手恢复呢?显而易见的,他们会把一切都炸光,显而易见的,在炸光以后他们会逃跑,而且显而易见的,我们今后会建筑得比以前更好!同志,那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他感到窘困,脸红得象个少年人一样。
“哦,假如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第一个发言的大个子喃喃地说。“好吧,同志们,让我们起来吧!你们还没听到德国鬼子正在向我们走来吗?”
真的,冲锋枪声越来越近了。德寇大概开始扫荡树林了。
我们并没有立刻就分散。我们这支十个人的小队又继续游荡了两天。我们侦察,向遇到的人打听德寇的所在,和怎样过去比较妥当。
这里的树林是稀疏而混杂的,常有草地和沼泽间隔。鸟儿时常在我们的头上飞向南方。
黄叶正在纷纷落下来,天又在下毛毛雨,树林变得愁眉哭脸,我们大多数的心境虽然不是郁郁寡欢,却是委屈苟安的。
我们不轻于谈到自己,而且也不乐意谈,第二天我才发觉我们这一队的伊凡·西蒙年科中尉是位党员。他说,在战前曾在乌克兰共产党(布)沃伦省委会当过指导员。我提起了一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