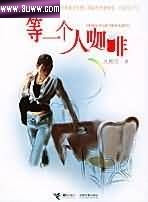上午咖啡下午茶-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千上万茶农参与的现代斗茶活动的缩影,是一幅活生生的现代风俗画。
宗璞:风庐茶事
茶在中国文化中占特殊地位,形成茶文化。不仅饮食,且及风俗,可以写出几车书来。但茶在风庐,并不走红,不为所化者大有人在。
老父一生与书为伴,照说书桌上该摆一个茶杯。可能因读书、著书太专心,不及其他,以前常常一天滴水不进。有朋友指出“喝的液体太少”。他对于茶始终也没有品出什么味儿来。茶杯里无论是碧螺春还是三级茶叶末,一律说好,使我这照管供应的人颇为扫兴。这几年遵照各方意见,上午工作时喝一点淡茶。一小瓶茶叶,终久不灭,堪称节约模范。有时还要在水中夹带药物,茶也就退避三舍了。
外子仲擅长坐功,若无杂事相扰,一天可坐上12小时。照说也该以茶为伴。但他对茶不仅漠然,更且敌视,说“一喝茶鼻子就堵住”。天下哪有这样的逻辑!真把我和女儿笑岔了气,险些儿当场送命。
女儿是现代少女,喜欢什么七喜、雪碧之类的汽水,可口又可乐。除在我杯中喝几口茶外,没有认真的体验。或许以后能够欣赏,也未可知,属于“可教育的子女”。近来我有切身体会,正好用作宣传材料。
前两个月在美国大峡谷,有一天游览谷底的科罗拉多河,坐橡皮筏子,穿过大理石谷,那风光就不用说了。天很热,两边高耸入云的峭壁也遮不住太阳。船在谷中转了几个弯,大家都燥渴难当。“谁要喝点什么?”掌舵的人问,随即用绳子从水中拖上一个大兜,满装各种易拉罐,熟练地抛给大家,好不浪漫!于是都一罐又一罐地喝了起来。不料这东西越喝越渴,到中午时,大多数人都不再接受抛掷,而是起身自取纸杯,去饮放在船头的冷水了。
要是有杯茶多好!坐在滚烫的沙岸上时,我忽然想,马上又联想到《孽海花》中的女主角傅彩云做公使夫人时,参加一次游园会,各使节夫人都要布置一个点,让人参观。彩云布置了一个茶摊,游人走累了,玩倦了,可以饮一盏茶,小憩片刻。结果茶摊大受欢迎,得了冠军。摆茶摊的自然也大出风头。想不到我们的茶文化,泽及一位风流女子,由这位女子一搬弄,还可稍稍满足我们民族的自尊心。
但是茶在风庐,还是和者寡,只有我这一个“群众”。虽然孤立,却是忠实,从清晨到晚餐前都离不开茶。以前上班时,经过长途跋涉,好容易到办公室,已经像只打败了的鸡。只要有一盏浓茶,便又抖擞起来。所以我对茶常有从功利出发的感激之情。如今坐在家里,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小人在土上的“坐”家,早餐后也必须泡一杯茶。有时天不佑我,一上午也喝不上一口,搁在那儿也是精神支援。
至于喝什么茶,我很想讲究,却总做不到。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花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五义》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因因的。”这几年不知何故,芳踪隐匿,无处寻觅。别的茶像珠兰茉莉大方六安之类,要记住什么味道归在谁名下也颇费心思。有时想优待自己,特备一小罐,装点龙井什么的。因为瓶瓶罐罐太多,常常弄混,便只好摸着什么是什么。一次为一位素来敬爱的友人特找出东洋学子赠送的“清茶”,以为经过茶道台面的,必为佳品。谁知其味甚淡,很不合我们的口味。生活中各种阴错阳差的事随处可见,茶者细微末节,实在算不了什么。这样一想,更懒得去讲究了。
妙玉对茶曾有妙论,“一杯曰品,二杯曰解渴,三杯就是饮驴了”。茶有冠心苏合丸的作用那时可能尚不明确。饮茶要谛应在那只限一杯的“品”,从咂摸滋味中蔓延出一种气氛。成为“文化”,成为“道”,都少不了气氛,少不了一种捕捉不着的东西,而那捕捉不着的,又是从实际中来的。
若要捕捉那捕捉不着的东西,需要富裕的时间和悠闲的心境,这两者我都处于“第三世界”,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何为:佳茗似佳人(1)
中国的茶文化是一门高雅的学问,品茗乃韵事也。小时候爱喝家乡自制的桂花茶,只觉得甘芳好喝,不知品茶为何事。及长,烟与茶俱来,饮茶也只是因为烟吸多了解渴而已。茶香似不及烟香诱人,尽管有烟瘾者是少不了要饮茶的。吸烟四十余年,现已戒绝五载,总觉得若有所失,生活中减少了一大乐趣,这时候茶叶就显得分外重要,渐渐体会到苏东坡诗句“从来佳茗似佳人”的譬喻之妙。
中国的茶叶品种繁多,各取所需,不遑细述。30年前初到福州时参观茶厂,进入门帘严严的窨制茉莉花茶工场,骤觉浓烈的花香袭人,几乎令人晕眩。福州花茶名扬海内外,确有其齿颊留芳的独特风味。不过饮茶总以茶叶自身为上,一切形形色色花香窨制的茶叶,除茉莉花茶以外,余如玉兰花茶,玫瑰花茶、珠兰花茶、柚子花茶和玳玳花茶等等,虽然各有自己的香味和风韵,而茶叶的原味则大为减色。《群芳谱》载:“上好细茶,忌用花香,反夺其味,是香片在茶叶中,实非上品也。然京、津、闽人皆嗜饮之。”至于摩洛哥等国家用中国绿茶加重糖和新鲜薄荷叶子煮而饮之,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了。
我喜欢头春新绿,这是清明前焙制的绿茶。狮峰龙井或洞庭山碧螺春新茶当然是佳茗,然其上品殊为难得。50年代在前辈作家靳以家里啜饮龙井新茶,沏茶饷客时,主人说这是方令孺特地从杭州托人捎来的。方是一位前辈女作家。当时只见茶盅的边缘上浮绕着翠碧的氤氲,清亮鲜绿的龙井茶叶片透出一种近乎乳香的茶韵。我慢慢啜饮,冲泡第二次时,茶叶更加香醇飘逸,那堪称极品的龙井茶至今难忘。有时一杯茶可铭记一生。遗憾的是龙井茶泡饮三次后便淡而无味。碧螺春比龙井耐泡,新茶上市时,饮碧螺春也是不可多得的美的享受。这两种茶叶倘若是真正的极品,历来售价奇昂,即或有那么一斤半斤,多半是用来馈赠亲友的。
入闽后,每年春茶登场,我倒是常有机会,以较为廉宜的价格,从产地直接向茶农购得上好绿茶。绿茶不易保存,储藏如不得法,时间稍久便失去色香味。因此新茶一到,最好不失时机地尝新。试想在春天的早晨,一杯滚水被细芽嫩叶的新茶染绿,玻璃杯里条索整齐的春茶载沉载浮,茶色碧绿澄清,茶味醇和鲜灵,茶香清幽悠远,品饮时顿感恬静闲适,可谓是一种极高的文化享受。面对绿莹莹的满怀春色,你感到名副其实的在饮春水了。
每一个饮春茶的早晨仿佛是入禅的时刻。
我总认为,福建的功夫茶才是真正的茶道,陆羽的《茶经》便对功夫茶有详尽的记述。烹饪工夫茶,茶具以宜兴产者为佳,通常一茶盘有一壶四杯,壶盘器皿皆极精巧,“杯小而盘如满月”,“且有壶小如拳,杯小如胡桃者。”到闽南一带做客时,主人辄以功夫茶奉客,先将乌龙茶装满茶壶,注入沸水后,加盖,再取沸水遍淋壶外。此时茶香四溢,乃端壶缓缓斟茶,挨次数匝入杯内,必使每杯茶汤浓淡相宜。饮茶时先赏玩茶具,次闻茶香,然后细口饮之。这一番过程便足以陶冶性情,更不用说那小盅里精灵似的浓酽茶汤了。尝见闽南一业余作者到省城修改剧本,随身携带小酒精炉烧开水,改稿时照烹功夫茶不误,怡然自得,乍见为之惊叹。据说闽南有喝功夫茶至倾家荡产者,也有饮茶醉倒者,可见爱茶之深。
日本茶道无疑是从中国的功夫茶传过去的。他们有一整套繁文缛节的茶道仪式,崇尚排场,近乎神圣了。在日本的家庭里做客时,奉侍茶道就随便得多,也简单得多。不论繁简,茶道用磨研成粉末后泡制的浓茶是苦涩的。不过细加品尝,确乎也有几分余甘足供回味。
旅闽岁月久长,尤其是这几年戒了香烟后,对半发酵的乌龙茶家族中的铁观音就更偏爱了。铁观音的魅力倒不在于乌润结实的外形,它的美妙之处是茶叶有天然兰花的馥郁奇香,温馨高雅,具有回味无穷的茶韵,是即所谓观音韵。
何为:佳茗似佳人(2)
我的生活中赏心乐事之一,便是晨起一壶佳茗在手,举杯品饮,神清气爽。一天的写作也常常是品茗开始的。最好是正宗的超特级铁观音,琥珀色的茶汤入口清香甘洌,留在舌尖的茶韵散布四肢百骸,通体舒泰。此时以佳茗喻佳人遂愈见贴切,铁观音真是丽质天生、超凡脱俗、情意绵长、举世无双了。
今春从香港带来台湾产的铁观音,取名“玉露”。湖绿色的圆茶罐,用墨蓝的棉纸包裹,衬以带着白斑点的鹅黄色夹层纸,外面的白色包装上是明人唐寅的山水小品,古趣盎然。文字部分力求雅致,说:“冲泡与享用佳茗,是一种由技术而艺术,艺术而晋至一种奇妙境界的历程,贯穿这个历程的基本哲理在得一个‘静’字。”好一个“静”字!这段文字深得广告术之三昧,别具匠心。开罐泡饮,茶汤呈嫩绿色,茶叶中依稀也有几分观音韵。奈何橘枳有别,总不如得天独厚在安溪本土出产的铁观音味道纯正。据说在台湾类似的铁观音很多,有一种叫“春之韵”的,这一芳名庶几配得上佳人之称。
“从来佳茗似佳人”,确是千古绝唱,此生若能常与佳茗为伴,则于愿足矣。
周作人:喝 茶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而且一定说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在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罢了。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葛辛(George Gissing)的《草堂随笔》(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确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支那饮茶已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则我殊不以为然,红茶带“吐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 of Tea,1919)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功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惟是屋宇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