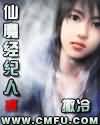茶与人-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由于受到周瘦鹃先生的感染,我在逛小古董店的时候,便对紫砂盆和紫砂壶特别注意,似乎也有了一点鉴赏能力。但也只看看罢了,并无收藏的念头。
有一天,我也记不清是春是夏了,总之是三十三年前的一个中午。饭后,我照例到那小古董店里去巡视,忽然在一家大门堂内的小摊上,见到一把鱼化龙紫砂茶壶。龙壶是紫砂壶中常见的款式,民间很多,我少年时也在大户人家见过。可这把龙壶十分别致,紫黑而有光泽,造型的线条浑厚有力,精致而不繁琐。壶盖的捏手是祥云一朵,龙头可以伸缩,倒茶时龙嘴里便吐出舌头,有传统的民间乐趣。我忍不住要买了,但仍需按约法三章行事。一是偶尔为之,确实,那一段时间内除掉花两毛钱买一朵木灵芝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买过。二是有实用价值,平日写作时,总有清茶一杯放在案头,写一气,喝一口,写得入神时往往忘记喝,人不走茶就凉了,如果有一把紫砂茶壶,保温的时间可以长点,冬天捧着茶壶喝,还可以暖暖手。剩下的第三条便是价钱了,一问,果然不超过一元钱,我大概是花八毛钱买下来的。
第二部分 观察陆文夫 得壶记趣(2)
卖壶的人可能也使用了多年,壶内布满了茶垢,我拿回家擦洗一番,泡一壶浓茶放在案头。
这把龙壶随着我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度过了很多寒冷的冬天,我没有把它当作古董,虽然我也估摸得出它的年龄要比我的祖父还大些。我只是把这龙壶当作忠实的侍者,因为我想喝上几口茶时它总是十分热心的。当我能写的时候,它总是满腹经纶,煞有介事地蹲在我的案头;当我不能写而去劳动时,它便浑身冰凉,蹲在一口玻璃柜内,成了我女儿的玩具,女儿常要对她的同学献宝,因为那龙头内可以伸出舌头。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要破四旧,我便让龙壶躲藏到堆破烂的角落里。全家下放到农村去,我便把它用破棉袄包好,和一些小盆、红木小件等装在一个柳条筐内。这柳条筐随着我来回大江南北,几度搬迁,足足有十二年没有开启,因为筐内都是些过苦日子用不着的东西,农民喝水都是用大碗,哪有用龙壶的?直到我重新回到苏州,而且等到有了住房的时候,才把柳条筐打开,把我那少得可怜的玩艺拿了出来。红木盆架已经受潮散架了,龙壶却是完好无损,只是有股霉味。我把它擦一番,重新注入茶水,冬用夏藏,一如既往。
近十年间,宜兴的紫砂工艺突然蓬勃发展,精品层出,高手林立,许多著名的画家、艺术家都卷了进去。祖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兴起了一股紫砂热,数千元、数万元的名壶时有所闻,时有所见。我因对紫砂有特殊爱好,也便跟着凑凑热闹,特地做了一只什景橱,把友人赠给和自己买来的紫砂壶放在上面,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小古董店可逛了,休息时向什景架上看一眼,过过瘾头。
我买壶还是老规律,前两年不超过十块钱,取其造型而已。收藏紫砂壶的行家见到我那什景架上的茶壶,都有点不屑一顾,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我说有一把龙壶,可能是清代的,听者也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什么收藏,连藏书也是寥寥无几。
1990年5月13日,不知道是刮的什么风,宜兴紫砂工艺二厂的厂长史俊棠,制壶名家许秀棠,以及冯祖东等几位紫砂工艺家到我家来作客,我也曾到他们家里拜访过,相互之间熟悉,所以待他们坐定之后便把龙壶拿出来,请他们看看,这把壶到底出自何年何月何人之手,因为壶盖内有印记。他们几位轮流看过后大为惊异,这是清代制壶名家俞国良的作品。《宜兴陶器图谱》中有记载:“俞国良,同治、道光间人,锡山人,曾为吴大溦造壶,制作精而气格混成,每见大溦壶内有‘国良’二字,篆书阳文印,传器有朱泥大壶,色泽鲜妍,造工精雅。”我的这把壶当然不是朱泥大壶,而是紫黑龙壶。许秀棠解释说,此壶叫作坞灰鱼化龙,烧制时壶内填满砻糠灰,放在烟道口烧制,成功率很低,保存得如此完整,实乃紫砂传器中之上品。史俊棠将壶左看右看,爱不释手,拿出照相机来连连拍下几张照片。客人们走了以后,我确实高兴了一阵,想不到花了八毛钱竟买下了一件传世珍品,穷书生也有好运气,可入聊斋志异。高兴了一阵之后又有点犯愁了,我今后还用不用这把龙壶来饮茶呢,万一在沏茶、倒水 、擦洗之际失手打碎这传世的珍品,岂不可惜!忠实的侍者突然成了碰拿不得的千金贵体。这事儿倒是十分尴尬的。
世间事总是有得有失,玩物虽然不一定丧志,可是你想玩它,它也要玩你;物是人的奴仆,人也是物的奴隶。
第二部分 观察李国文 张洁得壶(1)
大年初一,张洁打来电话,她得了一把名壶。这件时大彬的壶,如果不是赝品的话,那数百年的历史,虽说不得价值连城,但所值不菲,是当然的了。可她砍下来的价,说来令人笑掉大牙,连同另一把壶,统共花了一百二十元。所以,我说她“得”壶,而不是说她“买”壶。按一般道理,买和卖,双方应该是等价交换。物超所值,有可以能,但超出太多,超到邪乎的程度,那就该是得了。得,不必等价,也无须等价,因为,无论是得到一份爱情,得到一份幸福,得到一份意外的惊喜,都是没办法折算成人民币若干元的。她这次得壶,很大程度上是意外,是侥幸,是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无意中得之,很难用六十元衡量出壶的轻得高低。所以,她说,她是凭一种感觉,得到了这把名壶。我说,我要写一写她得到这把名壶的故事,谈谈那一霎那产生的直觉。直觉,是一种很奇怪的体验,有时候,很准,立刻就产生出一种心灵感应。她感觉到这是个好东西,结果,一把时大彬的壶到手了。
就我个人而言,对于紫砂壶,所知甚少,连时大彬这位明末清初的制壶老祖,也只留下一点极肤浅的印象。那一年,到宜兴去,应景也曾背回几件,陆续都送了朋友。因我爱茶,却不甚爱壶,我认为喝茶,不光是嘴巴的事,眼睛,鼻子都要参与的。所以,茶叶在透明的玻璃杯里,上下浮沉,渐渐地舒张开来,慢慢飘舞起来,那一股难以描摹的灵动神韵,真是视觉上的极佳享受。尤其春天里刚下来的新茶,领教那一份洋溢开来的绿,更是心旷神怡的境界。如果用壶的话,对不起,这一切便全部等于零,茶趣也就少掉一半。
张洁得壶,过程简单。年前,她本是准备到天坛去买熬中药的药罐,走过一地摊前,瞥了一眼放在那里的玉石之类,伫足停下,摊贩为一老先生,便向她推销谁知是真的还是假的翡翠。张洁似乎懂一点珠宝,我记得她写过一篇小说,就叫《祖母绿》。不过她是不是行家,我就不得而知了。即使非行家,又如何?我一直认为,作家写东西,凡涉及到专业知识,只求能把读者唬住就行,不一定必是行家里手。
所以,曹禺《日出》的第三幕,为写那个雏妓小东西,在窑子里的生活状态,是到过前门八大胡同——旧时代北平城的红灯区的;巴尔扎克写交际花,也曾和一些巴黎社交场合的名女人,有过交往,但也仅如此而已。一定要有一份专业证书才可写某行某业,那么,大部分作家就得饿饭了。她对那位老先生说,慈禧太后才戴多大一块翡翠,你这摆的,哪一块都超过了她,如果是真翠,也就不会在这儿摆摊了。这时,张洁见到了旁边摆着的这把泥污斑渍,积满茶垢的壶,顿觉眼睛一亮。在电话里,她没有这样说,但我相信她见到这把壶时,肯定应该是这种样子的。因为她说她当时有一种感觉,虽然,那壶很脏,很糟,跟泥蛋一样,半点也不起眼,但壶的造形,虽然与别的壶同是由圆弧和曲线构成的整体,同是盖、嘴、把、壶本体四个部分,隐约间,那颇有些不同凡俗的气质,把她打动。孟夫子曰:“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但她终究是西子呀!天生丽质,总是不可能全被埋没的,这就要求观察者有没有一双慧眼了。 据我了解,她没有收集古玩和文物的癖嗜,之所以想得到这把壶,她强调,就是认准了自己这个直觉,决定要买下来。摊主出价,两壶各一百,你拿走。她按照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惯例,先砍一半。这笔生意,谈到最后,以每把六十元成交。他告诉张洁,壶是从天津倒腾来的。这一来历,令我顿生疑窦,因为无论博物院收藏的,还是近年发掘出来的大彬壶,都出在南方,北方甚少见。直到今天,紫砂壶在北方不如南方受欢迎,我想,很可能是与北方人喝茶不甚讲究有关,北方人喝茶习惯,深受蒙古族、满族影响,粗疏而乏精致,大碗茶三字,便可概括。那淡淡的绿茶清香,绝敌不过那性膻味骚的牛羊肉的,必须是浓郁的花香,方可压住大蒜大葱韭菜花的恶辛之气。我刚到北京时,参加京西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旗人家里,初次喝到香喷喷的茉莉花茶时,甚觉惊异,花香浓烈若此,还能叫作茶嘛?六十年代,八毛钱一两的茉莉高碎,竟成了北京市民的至尊至高的享受。对茶的不考究,导致对壶的无兴趣,很难设想一件名家的壶,会在并无久远历史的天津出现?
但转而一想,旧时代,天津为商埠,多富翁;北京为衙门,多官僚。很可能是清末民初天津租界地洋房里住着的某位阔佬,从北京城某胡同,某四合院里,某败落户手中买去的。老北京,不论什么样破旧颓败的院落,走进去打听打听那些老住户,不出三代以上,准是显赫的王公贵族。五十年代,我在北京,住在苏州胡同,隔壁院里老太太卖破烂,堆在屋角的熬汤的大骨头中,竟混有羚羊角。那敲小鼓的还算仁义,用小刀刮去泥垢,“老太太,您这可是值钱的东西,我当破烂收了,蒙了您,我也亏心,您拿到药铺去卖吧!”所以,京城破落户有这把时大彬的壶,不为奇,往前再追溯上去,很可能是明代南方某位上京做官,或来京行贿的什么人带来。后来,败家了,就流失民间,又被天津这位有钱的阔佬买到手。
第二部分 观察李国文 张洁得壶(2)
壶若能言,这一段由南而北,由京而津的路线,肯定会讲出一连串人事兴衰,沧桑变化的故事,若是编成电视剧,或许可以在泛滥成灾的皇帝片中,别开生面,凑一份热闹。从这件壶跌落到天坛地摊上无人问津,也证明了一条真理,这世界上没有永远。好多人,包括我们作家,都以为自己会永远,或将会永远。读一读台湾的白先勇先生写过一篇精致的短篇小说,叫《永远的尹雪艳》,便会晓得,其实那女主人公也不能永远,终于到了蚌老珠黄的这一天。天津租界地的这位富翁,最后,子孙不也衰败,把茶壶当油壶。当初,富翁为买这把名壶,可能所费不赀,至少他还识货,知道附庸风雅,多少年以后,他的后代却不经意地把名壶三文不值二文地卖了。说不定这家住过洋楼的后代,不但不知道这是把名壶,甚至压根儿不懂壶为何物,用来装油,那就更悲哀了。
天津和北京住户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