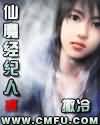茶与人-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茶叶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内在质量。受到产地的土壤状态,水质条件,栽培方法,采摘时间,以及日照,云雾,湿润,微量元素等等因素的制约,一方水土,出一方茶叶,所以,龙井茶的饮誉千年,是和龙井这个地方分不开的。因此,龙井的龙井,与杭州的龙井,与杭州以外的龙井,应该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的。
明人田艺蕻《煮泉小品》中说道:“今武林诸泉,惟龙泓入品,而茶亦惟龙泓山为最。又其上为老龙泓,寒碧倍之。其地产茶,为南北绝品。”可见古人也已经明白,所谓龙井茶,也只有狮峰、龙井、梅家坞这几处出产的,才是最地道,最本色的龙井茶。
去年春末夏初,北京城里好几家商场、茶庄,就有现场炒茶的表演。茶叶是飞机空运来的,炒茶的师傅自然也是产地请来做示范的。因为成本太高,价格不菲,也是围观者多,购买者少。我也挤在其中欣赏师傅的操作,在啧啧称羡声中,那新炒出的茶,沏出来,你会联想到一首抒情诗,一幅水墨画,一支提琴独奏曲,有美不胜收之感。
但是,再好的师傅,炒出来的再好的茶,是龙井,就是龙井,不是龙井,就不是龙井。当然,真正龙井,其上品,是不大容易买到的了。如今那些标明龙井的龙井茶,很大部分并不是龙井生产的,而且来自杭州四周,来自离杭州更远的地方,也未可知。看来龙井之大,简直无边无涯了。
不过,端在手中的这杯非龙井产地的龙井,其实,应该属于上品。否则,我的朋友不会特地给我带来,不会信心十足地当场沏出来,大有真金不怕火炼之意。他说了一句上海话,“灵勿灵当场试验”,果然好茶,是不用说的了。然而,滋润肺腑,腋下生风之际,我也不胜其惶惑,这间茶厂,能生产出这等优质茶,既然不想以次充好,既然不想以假作真,既然不亚于名茶,或者哪怕亚一点,也没有必要非附骥于名茶不可呀?
我与来客讨论,若从心理层次探究的话,这些所作所为的背面,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缺乏自信的表现。
于是,浮想联翩,茶,如此,其实,人,何尝又不如此呢?
在生活中,好端端的人,有时硬是不十分相信自己,也是屡见不鲜的。非要依托于名人,借重于洋人,仰仗于要人,赖靠于死人,惟如此,才觉得脸面有光,才觉得自己人五人六,这实在是很累心累力,也是大可不必的事。
说到底,你就是你,你就做你自己,那多好?
第一部分 行动李汉荣 品茶
茶,是最朴素、淡泊的美物。饮茶,是最朴素、淡泊的美事。
在一间陈设简单、干净、空旷的小屋里饮茶是最好的。华贵、复杂的房间里不宜饮茶,那高大、贵重的东西在茶面前摆谱、显阔,茶的自然气息就被埋没了。
饮茶的时候,心情越平淡越好。心情平淡的人,才能感受茶带来的宁静和清新。
每一片绿叫—都在高山深谷里浴过风雨云雾,听过鸟声虫鸣。简单的叶子,却有着绝不简单的经历。但它们是沉默的,在滚烫的水里它们并不发出惊叫,接受了这过于热烈的邀请,它们慢慢吐露出纯洁而芳香的情愫。
此刻的杯子里漾出碧绿和淡淡的清香。在这个时候,茶是最香的,但在这个时候,我常常不忍将嘴唇交给茶杯。茶的一生,就这样了结了么?我想起人生的种种细节,想起那珍藏在这些细节里的眼泪、微笑、期待和感动。就这么喝下去?茶的一生就这么毁于一旦?
于是,我默默向茶感恩,向生活和大自然的每一个细节感恩。向云雾中采茶的那双小手感恩—厂那是我的妹妹,在鸟声和微风里站着,她伸出手,和着露水采下了一生中最纯洁的瞬间,采下了天空中渐渐呈现的一角蔚蓝,然后,她哼着一首险些失传的民间小调,将满捧的绿色盛进竹篮,盛进别人的生活和日子,盛进我的日子。此刻我的杯子里,那浮动的叶片上,印满她的手纹。
我的眼睛湿了。想不到,在这么一个平静的时刻,我流下了这么深刻和纯洁的眼泪。于是我忽然想到:我杯子里盛的是茶的泪水。
泪眼望着泪眼。我喝下了茶水,我接受着这感人的馈赠。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不仅为事物的色、香、味、形所惑,而且联想到事物不平凡的来历和它们蕴含的艰辛、忍辱、牺牲等等内涵,当我们遭遇这些事物的时候,就是与生命和命运遭遇。这些事物就不仅进入了我们的身体,而且深入了我们的灵魂。
世界不只是一堆物,世界更是一个比物更丰富、更恒久,也更惊心动魄的精神过程。我们透过物的“物性”,看到的是更其深广和神秘的“神性”。一件物到达我们面前,它不仅吁请们感受它自身,而且期待我们体悟与它关联的一切。
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它更是一种有意味的事物。饮茶,就不只是为解渴和去乏,更是要感受在茶的氛围里所呈现的境界、情调和韵味,有时要达到一种智慧和觉悟。
由茶,我们可以推想到许多。一株树不仅是供我乘凉和做家具的,一株树也是一种意境,一种生命的境界,树根在深深的地下展开着纠结着,它使我们联想到生命的明亮部分往往由其幽暗乃至苦难的根基所营养,由此才有树,冠那巍峨葱茏的生命高峰。一头奶牛也不只是供我们挤奶的动物,它也有感情、有痛苦,如果不是人的挪用,也许这奶牛早已做了母亲了,我们享用的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牛奶正是奶牛用苦痛所酿就。生命的成长是这样美好,而其背景又是如此艰辛甚至带着残酷,当我们喝完了牛奶,是不是不仅只增加自己的几分脂肪和体力,而且也增加一些德性:对大自然、对生灵多一些珍重和怜悯。我们被其他生命养育着,为了我们活着,许多生灵承担了苦痛。如果我们再额外地为大自然和生灵增加痛苦,我们就大大地错了。
人的一生要喝多少茶,茶里的香味、甘味、涩味、苦味、意味、禅味,我们能品出多少?从第一杯茶到最后一杯茶,由浓郁到平淡,由浅尝到深品,永远有品头,永远品不到尽头。即使生命到了尽头,最后那杯茶,仍如最初的那杯眨着绿的、深长的眼神……
行动周作人 吃茶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英文译作,(Teaissm)而且一定说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现.罢了。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葛辛(GeorgeGissing)的《草堂随笔》(原名pers?fHenryRyecroft)确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支那饮茶已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则我殊不以为然。红茶带“土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ofTea,1919)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工夫茶者自然更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惟有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可吃的东西应当是轻淡的“茶食”。中国的茶食却变了“满汉饽饽”,其性质写“阿阿兜’’相差无几,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的“羊羹”(据上田恭辅氏考据,说是出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尤有特殊的风味。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为“堂倌”所独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在南京时常食此品,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虽也曾尝试,却已忘记,所记得者乃只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式,因为一到即罄,次碗继至,不遑应应酬,否则麻油三浇,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欢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乡昌安门外有一处地方名三脚桥,(实在并无三脚,乃是三出,因以一桥而跨三汊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制茶干最有名。寻常的豆腐千方约寸半,厚可三分,值钱二文,周德和的价值相同,小而且薄,才及一半,黝黑坚实,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脚桥有步行两小时的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担设炉镬,沿街叫卖,其词曰:
辣酱辣,麻油炸,
红酱搽,辣酱拓;
周德和格五香油炸豆腐干。
其制法如上所述,以竹丝插其末端,每枚三文。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软,大约系常品,唯经过这样烹调,虽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为一种好豆食——豆腐的确也是极乐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种种的变化,唯在西洋不会被领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饭,名曰“茶渍”;以腌菜及“泽庵”(即福建的黄土萝卜,日本泽庵法师始传此法,盖从中国传去)等为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风味。中国人未尝不这样吃,惟其原因,非由穷困即为节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为可惜也。
第一部分 行动周作人 吃茶二
吃茶是一个好题目,我想写一篇文章来看。平常写文章,总是先有了意思,心里组织起来,先写些什么,后写什么,腹稿粗定,随后就照着写来,写好之后再加,一题目,或标举大旨,如《逍遥游》,或只拣文章起头两个字,如“马蹄秋水”,都有。有些特别是近代的文人,是有定了题目再做,英国有一个姓密棱的人便是如此,印刷所来拿稿子,想不出题目,便翻开字典来找,碰到金鱼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