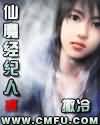茶与人-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杯茶,只不过是想争那一口气罢了,而今,当真争“赢”了,却又觉得捧在手里那杯茶特别可口,特别香醇。拂面的轻风夹杂着桑葚成熟了的那一股甜香的气息,仰头看时,颗颗桑葚宛如粒粒小巧玲珑的绿玉,在午后温煦的阳光里闪着一圈一圈可爱绝顶的笑影。站了起来,摘了一串,吃,哇,甜入心坎!
那天,在那间露天茶室,足足坐了三个小时,喝了整十杯茶,以自助方式吃了无数无数桑葚;啊,那种什么也不做、“时而千思时而无思”的感觉竟是如此难忘而美好。
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伊朗人将茶喝成了生命里一道不变的美丽风景。
第二部分 观察牧 惠 说广东的叹茶(1)
谁如果去过广州而不曾上过茶楼叹茶,夸张点说,等于白走一趟。
我是在广西长大的广东人。广东地少人多,有点门路的,都纷纷出外谋生。办法多一点的,到美国、加拿大或南洋、港澳一带;办法少一点的,到广西打工做生意。广西南部的市镇,当官、当地主的基本上是讲桂林官话的本地人,做生意的大都是讲粤语的广东人或他们的后裔。凡是广东人生活的地方,哪怕是美国的唐人街,或广西的一个几千人的小镇,都必定有茶楼。我从懂事起就知道有茶楼。我们家穷,打工的父亲不会带我上茶楼;外祖父是医生,也不肯带我这样的小把戏上茶楼。我对茶楼的认识,从外祖母上茶楼带回给我的肉包子、鸡蛋糕开始。母亲是外祖母的独生女。母亲结婚生子后,外祖母三天两头到我们在陈家巷租住的钟家大屋看我们,有时就带来这类点心。那包子给我的印象很深,它跟北京的包子不一样,一是包子皮特别甜和松,那馅是切成丁的鸡肉、蛋黄、马蹄、香茹,味道比搅成一团的肉末白菜鲜美多了。于是我得到一个印象:茶楼有好点心吃。
喝茶同时吃点心,这是广东茶楼同北京、四川等地茶楼的根本差别。说到这里,我不妨讲个笑话。记不得是哪一年了,画家廖冰兄、韩羽等老友来北京搞什么活动。我打电话给冰兄女儿陵儿,请她约朋友们到大三元饮早茶聊聊天。冰兄是个聋子,因此必然是个“大声公”。他一见面就哈哈大笑揭韩羽的短:韩羽一大早对他说,牧惠请我们喝茶,咱们要不要吃完早餐再去。搞得大家笑,韩羽也笑。他是“北佬”,哪能知道广东人的“饮茶”同“北佬”有什么区别?
这是几十年后的一段小插曲,整个小学时代,我却一直无缘上茶楼。关于茶楼的知识,都从家里富裕、年纪比我大得多的同学那里略知一二。那时当地的茶楼的经营方式跟现在略有不同。客人到茶楼时,桌上已经摆满给客人准备好的“星期美点”,即每周换一次的各种点心。除了另叫的如炒粉、炒饭之类的食物外,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吃桌上的包子、烧卖,吃完后伙计收拾吃掉点心的碟数后,马上大声吆喝消费了多少钱让收款处结账。那时的伙计练就一种本领,不必笔算,很快就可能准确无误地把客人的账目报得清清楚楚,绝不会发生错误。但是,个别顾客的恶作剧他们却防不胜防,例如包子,那时的包子都用一张跟包子一样大小的白报纸垫底蒸。淘气的顾客悄悄地掀开白报纸,从中取食包子馅,然后把它还原成并未动过的样子。这一来,不够醒目(他们只能用眼看,绝不可以用手捏一捏包子的虚实)的伙计就会吃亏。当然,这种客人是极个别的,但极个别当中,就有我这位自吹自擂的淘气同学。
后来上中学了,才终于领略到在茶楼饮茶的滋味。那时,为了逃避日本鬼子的轰炸,中学从县城搬到八步镇郊十来里的马鼻角。八步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小镇,自从发现它附近的水岩坝一带有丰富的锡矿和钨矿后,八步才成了远近闻名的大镇,有了电灯,有了繁荣的商业。就连红极一时的粤剧名伶马师曾,也率领他的剧团逃难到八步扎下根(红线女就是在八步唱红的)。于是,原先在贺街镇的生意人也纷纷转移到八步来。祖父和叔叔们也从贺街转到八步打工。这样一来,八步就成了我的一个落脚点。由家里去学校,路经八步;星期天休息,三五成群地到八步玩耍。八步有一间比贺街的小茶楼宏伟得多的一处茶楼,是我们饮茶吃点心的好地方。有时是同学请客,有时是祖父或叔叔买单,有时是报馆的编辑(他们往往刚刚睡醒)约我在那里见面谈稿子。在那里吃上一个包子,一盘炒牛河,补充一下缺油少肉的肠胃,其乐无穷。
但是,为什么上茶楼饮茶叫做“叹茶”?个中滋味,我是直到去了广州之后才算明白的。
“叹”者,在粤语中,除了“叹息”、“叹气”之类寓意不愉快心境的内容外,还有享受、享乐之类的用法。“叹世界”寓意过上舒心的日子,不必为住房、吃饭、穿衣之类琐事而犯愁。“叹茶”属于这类意思,其可“叹”之外远远不是点心之类可以包含的。
第二部分 观察牧 惠 说广东的叹茶(2)
在广州,大型茶楼如惠如、莲香等,门口肯定会有两三档报摊,除了卖报外,还经营租报。报贩给报纸涂上或红或绿或黄以资区别的颜色,茶客上茶楼时,随手从摊上取走自己想看的几种报纸。饮茶完毕后,按份数给予相当于报纸几分之一的租金。这样一来,茶客可以花一份报纸的钱读到好几份报纸,报贩的报纸租用完毕后再低价处理掉,来它一个“双赢”。“叹茶”的“叹”字,其中一项就是,你可以开上一客茶,在茶楼边仔细地品茶,边浏览各种报纸,同朋友聊天侃大山兼议论国是,骂骂蒋介石、宋子文啦,传播“拍错手掌,烧错炮仗,迎错老蒋”之类民谣啦,有什么最新小道消息听,一扯就是一个小时,有的还达半天。熙熙攘攘,热闹得迟到的居然找不到位子(茶瘾大的,早上四、五点就来占位了),走了一批马上又有另一批来占位。那时有一种专门给报纸写专栏的文人,有的写杂谈之类短文,有的写连载小说。他们的作品,大都在叹茶聊天中得到灵感,当堂写下几百字一篇完稿。效率高的,甚至可以同时给几家报纸写专栏、写连载,小说主人公的喜怒哀乐,也往往在此时此地起了变化。总之,茶楼成了某些人一个重要的生活空间。当然,像我这样的穷学生,纯属偶然的过客,目的是直奔“星期美点”如鸡球大包之类,离“叹”尚远的。
离开学校,进到游击区之后,我才从另一个角度发现,叹茶之于广东人,吸引力竟是那么大。
游击队能如鱼得水地生存、发展的地方,大都是相对贫困的山村。但是,即使在这里,茶居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种事物。每村都有一间茶居(不叫茶楼,不知是一种雅称,还是相对来说规模要小多了?)是不可能的,一个有三百户以上的村庄,开一间兼营咸杂小百货的茶居,有本村的顾客,还有附近各村的顾客,肯定可以支持下去。这类茶居比较简单:摆上三五张八仙桌,玻璃缸里分别装有花生糖、芝麻糖、鸡仔饼、绿豆糕之类的干点心,偶然也做点包子之类供应,这就是一间茶居。为了工作需要,我不时地在这些地方同一些“大天二”之类的统战对象饮茶聊天,建立起友谊,然后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怎样说明“大天二”是什么人物呢?他们有枪甚至有马仔,但区别于土匪,也不像恶霸那样欺凌弱小。他们却是在当地说话算数连乡保长也惹不起的人物,赌摊、烟档主动按期交给他们叫作“规”的保护费。他们对“老八”(游击队即土八路)很客气,看不起乡保长。因此很乐意同我们交朋友,时不时约我到茶居饮茶。这时,按规矩,他总是蹲在正对着大门的条凳上。正对大门,有便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蹲而不坐,万一有什么敌情,可以保证他在第一时间站起来,同时拔出倒掖在裤带上的驳壳。两年时间,我陪他们饮茶次数数不清,幸运的是,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还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饮茶对于广东人的重要性。其一是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的佛坑茶居。佛坑不到一百户,但是,因忍受不了附近冯村大姓的欺侮,他们绝不去冯村茶居饮茶,自力更生地开了一间特别的、每天仅仅营业不到两小时的茶居。晨早,大家带着农具,先后来到这间茶居,边聊天边叹茶边等老板按大家报的数字蒸熟肉包子。包子得了,吃完,记上账,包括老板在内的全体村民都下田干活。其二是1958年我到新会城南一个高级合作社“三同”,结果是多了一同,同到茶楼饮茶:每天早上出工前,男社员们都到茶楼集中,在那里叹茶,同时听候队长分配活路,吃完早点后,一声呼啸,这才下地。
看到这里,读者肯定会抗议了:你讲了半天饮茶,广东茶楼有什么好茶叶好点心,你几乎根本不提,这就算交了卷?
谨答曰:饮茶的重点在于“叹”。一次来了几位日本客人,他们在广州住了一个月,要求每天早茶的点心不重复,酒家轻而易举地交了差。一一说来,岂不成了一本书?你想知道有什么好点心可吃,上茶楼“叹”一下就是了。
第二部分 观察王雷泉 赵州吃茶记(1)
一、庭前柏子待何人?
来参真际观音院,何幸国师塔尚存。
寂寂禅风千载后,庭前柏子待何人?
以上—诗,为净慧法师住持赵县柏林寺的感怀之作。柏林寺在唐代名观音院,从谂禅师长期行脚参学后,于八岁左右定居于此,任方丈达四十年,人称“赵州古佛”,寂后赠“真际大师”。赵州对前来求道者,不管是曾到还是新来,皆请人“吃茶去”。“赵州茶”、“云门饼”、“德州棒”、“临济喝”,自唐代起就风靡丛林,几成为中国禅宗的象征。净慧法师一九八八年以《法音》主编身份出长河北省佛教协会,即以一家《禅》刊,二座祖庭(临济寺与柏林寺)为中心,建构河北教团。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至二十六日在柏林寺举办了以大专青年为主体的“生活禅夏令营”,可说是中国大陆佛教界一次真正面向社会的主体性活动。如此殊胜机缘,岂可当面错过?我素不喜应酬,这次放下手中一应杂事,带着选修我的“佛教哲学”课的四位复旦同学,去领略“赵州茶”究竟是什么滋味。
与赵州同时代的雪峰义存禅师住锡南方,有学生问:“如何是古潭寒泉?”雪峰答:“即使你瞪目而视,也看不到底。”“那饮水的人怎么办呢?”“他不用嘴饮。”赵州得知这段对话后笑说“既然他不用嘴饮,也许用鼻饮吧。”人问:“那你说如何是古潭寒泉?”“味道很苦。”再问:“饮水人又如何?”赵州回答:“死法。”据说雪峰听至这话,大为赞许“真是古佛!”看来,这“赵州茶”不是那么好喝的,“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直须以超绝尘世的智慧烹煎寒泉,冲泡成慈悲济世的热茶,重新面对这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亦即禅家所谓“大死—番,再活现成”。
道不远人,触目即是。故当僧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