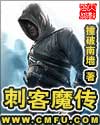��֮������-��4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Ϊ���Ŀ��ǣ���֮�����ѡ����·�ı�����������Զ��ͨ��������ֹ��ϵ��ʢ֮����������ת�ٻ����ͼ����ã�������˰�����������ɴ˶��������������Ͷ�����·�����У����������������ٻ��ӽ��У�ͽ����·��·֮�Ѷ������档���ٸ�����һ�������������飬�������Ӧ����«���������ڵĸ��ظ��ߡ���������ĵ籨�У���֮����һ����֤������·�����壺
������ν«��һ·�����й�ȫ·֮��١������ϵ����������Ӽ��֣���Ȩ��Ҫ�ڴˣ������������ڴˡ����Ƴ�ͨȫ����������֮������ĩҲ�������۽�Ч�����й���ʡ֮��������ԶЧ��ͨŷ����֮ת�ˣ�����·��֮���٣�����·��֮���ᡣ���ɴ˿ɼ�����֮������·Ϊ����֮����������˼�룬ҵ���γɡ����Ժ��ɵġ�Ȱѧƪ���У�����ר�١���·��һ�ڣ��������ڡ���ʿũ���̱���ѧ֮�š���������Ҫ��λ���ֹ�����·��ͨ������Ч�ܣ�һԻʡ���������տ���������Ȼ����ν����·һ���������β��գ�������������ʹ�����ҡ���ţ���Ǹ���ǣ�����������ơ���δ��������뻯����������·Ϊ����֮������������ʶ��ȴ���Ͻ����������������������ѡ������������벻����·Ŧ��������Э����չ�Ļ�����ʵ����Ҳ������������������ѣ�����«��·���������·��ֱ������֮�ʣ����Ȑ�������·���۵���ʶ������
������·֮�⣬��֮���Թ�·����Ҳʮ�����ӡ���˵����������֮������·��ΪҪ�壬��������Ѹ�٣���Ϣ��㣬�˻���ͨ�����������������ո����١�����ɽ��������������ͨ�����ƶ����㣬�ֽ���ͨ��·��Ϊ�������ϵ���ǰ�����̡��ܶ����㡢�����ڼ䣬��������·�����ȶ���������Щ������������ͨ˼������֡�
�����ۡ�ȫ����������ʮ�壬������ʮ�塣
�����ܡ�Ȱѧƪ����ƪ��ũ����ѧ�ھš���
�����١�Ȱѧƪ����ƪ����·��ʮ������
�����ڡ�ȫ����������ʮ�ģ�������ʮ�ġ�
�����ۡ�ȫ����������ʮ�ߣ�������ʮ�ߡ�
�����ܡ�ȫ����������ʮ��������ʮ��
�����١������ҹ�ȫ�顷�����ţ������ţ���34ҳ��
�����ڡ������ҹ�ȫ�顷�����ţ������ţ���35ҳ��
�����ۡ�ȫ����������ʮ�ߣ�������ʮ�ߡ�
�����ܡ�ʢ��Σ�ԡ����࣬��������1ҳ��
�����١�Ȱѧƪ����ƪ��ũ����ѧ�ھš���
�����ڡ�ȫ����������ʮ����������ʮ����
�����ۡ�ȫ����������ʮ�壬������ʮ�塣
�����١�Ȱѧƪ����ƪ��ũ����ѧ�ھš���
�����ڡ�ȫ����������ʮ�ߣ������ʮ�ߡ�
�����١�ȫ�����������ٶ�ʮһ�������ˣ����̲���
�����ڢۡ�Ȱѧƪ����ƪ��ũ����ѧ�ھš���
�����ܡ�ȫ�����������ٶ�ʮһ�������ˣ����̲���
�����ݡ������幫�ζ��ǡ���33ҳ��
������ˮҰ�Ҽ��������ڡ���
�����ڡ�����䷨����һ������143ҳ����250ҳ��
�����ۡ�ȫ����������ʮ�ߣ�������ʮ�ߡ�
�����ܡ�ȫ����������ʮ�ߡ�������ʮ�ߡ�
�����ݢޡ�Ȱѧƪ����ƪ��ũ����ѧ�ھš���
�����ߡ�ȫ��������һ����ʮ����빶�ʮ�š�
�����٢ڡ�ȫ����������ʮ�ģ�������ʮ�ġ�
�����ۢܢޡ�Ȱѧƪ����ƪ��ũ����ѧ�ھš���
�����ݡ������幫빸塷����ʮ�š�
�����٢ڡ���ʷ�塷��һ�ľţ���ͨһ����4430ҳ��
��
�����ڡ�ά��������Ȩ
�����йؾ��û��Ȩ�Ŀ��ǣ�����֮������˼��ĺ�������֮һ����������������߽������Σ�����˼�Ͻ��֮�ڵ��������ѳ�ԣ�йأ����뵱ʱ�й�������ǿ��ȡ����ľ�������֮��ֱ����ϵ���������������ԭ�����ľ�����Ȩ�ۣ��ִ��¿ɷ�Ϊ�������棬���������ϵ���棬��ȫ��ά���й���Ȩ��ʹ֮���ܻ�������ǿ���棻�ڹ��̹�ϵ���棬�������ڡ��١�������������Ϊ������������Ȩ�������ض�����£����ڳ�Զ�ġ�ͨ�̵Ŀ��ǣ�Ҳ��������̡����ṩijЩ�������Ӷ��ٽ�����乤��ҵ�ķ�չ��
������֮������˼��Ļ���˼���ǡ�������֮��������©ش��ԣ�������ڣ�����ھ��û�У���ʼ��עĿ��ά���й���Ȩ��������ǿ���̰�����ʴ��Ϊ�ˣ������һϵ�����š�
������һ�����ù�˰���ݹ��ߡ�
�����ڶ���ó���У���֮�����ż������������˰��������������������˰���Ա������幤��ҵ����˵�����鶫�������������Գ��������˰������ߣ���δ���Ա���֮����������֮����ͬһ�����������˰����������˰�ߣ�ͬһ��Ʒ��������˰������˰�����м��ؽ���˰���ڻ������˰֮�⣬���������н����������𡱢١���ָ����ŷ�����ձ������������˰���й���Ӧ�������С�
����Ϊ����߹����������������������֮��������������γ���˰�������ڹ�������ʱ����Ӧ����˰�塣������ʮ���꣨1896�꣩������һ�������н��飬�Թ�������������˰�Żݣ������к�����������ֹ켰�������ָ֡����ϣ����ڱ�ʡ����ʡ�Կ�ú��Ϊ������������֮�ã�Ӧ��������˰ʮ�꣬��ʱ�쿴����������������ɵ���������������˰�����ڶ�������������ҲӦ�մ˰��������Ⱥ�Ϊ��������֣���ұˮ�೧����������������˰�塣��֮���������������Ϊ�ȣ���˰ԣ��Ϊ�ۡ�
�����������չ���幤��ҵ���Բ�����������©ش��
������֮����������������ͨ���������й�֮�����������ߣ���ҩ���⣬Ī������ɴ��������Ȳ��ܽ��䲻����Ω�й�����������ɴ֯���������乤��֮�����Ա���Ȩ�������������Դ���ѶŶ���Ω���跨�������Ծ�֮���ݡ�����Ϊ���й����賧�ң�������������ɲ������������ά��������Ȩ�Ļ�������Ч�������Ҷ��һ��֮��������©һ��֮�ƣ���֮�վã�ǿ��֮�Ʊ���ת���������ߡ��١���֮��ָ�����������öȽϼ��������족����֮�й�����Զ������Ϊ�ͣ����ز�����ʡȴ���˷ѣ���һ�ж�ʮ���������Բ���Ʒ������ľ���������ʹ���̱������ȣ��������࣬���̼������Ѿ�������ren�ң�����Ϣ���������������������١��ڣ������©ش������������ԣ��
������������������ֹ����ʱ���·�����ҵ�����롣
����������Լǩ���Ժ�����ʱ�������ȡ����Ʒ���룬��Ϊ��ǿ�Ի��������Ե���Ҫ��ʽ������ʱ�ֱ���ڻ��賧��ҵ�������й���������������Խ����������ֵ��ͷ���ͣ����й���Ȩ��Σ������ޡ�����֮������֮������Ȼ���赲����ʱ��Ķ���֣������������·����ɽ�ȹ�ϵ��������������Ҫ�����ţ�Ӧ������ֹ���ʵ����룬�����Լ���Ȩ��֮�ڸ���ʵʩ��
������֮����Ϊ����Ω����Ϊ�й�����֮��Դ���ϲ��������˹�֮���ۡ���ˣ����ڹ�����ʮ���꣨1896�꣩��Ȼ�ܾ�Ӣ�����ȳ��̸��ɺϰ�ú�������Ҫ������������൱�̶��ϻ�������������ʽ��ȱ�����ٵ��յ�Σ���������Ժ���֮����֪������ɽ��ǿ����ɽ�������̺Ϲɡ����������ز���ȷ�в���������������족�����������ֹ�������ꡰ���������������������ɣ�ԭ�����϶����עܡ���������͢������鶨������������ʰ������������£���֮������ı��������ɣ��ڡ�������ְ䷢�ⶩ�����³̡��й涨���Ͻ����̶��ʰ쳧��ֻ���뻪�̺��ʣ����ҡ���ɷ�ֻ��ռһ�룬�������ڹٹ�֮��������������̲��ܳ����ҵ�����٣��ȵȡ�
��������·��ҵ�У���֮��ά��������Ȩ��̬�ȸ�Ϊ�������·����֮����Ϊ����֮�����������类������ݣ�����·������һ���ӣ���·������������������ӡ��ڡ���˵����·���죬���ȶ�Ȩ�������߲��족�ۡ����䱾�⣬«����·���л��̼���Ϊ�ʽ���Դ������ʡ�������м�����ǧ���������ߣ���������˾�������˰족�ܣ�����������Ӳ��֣���ȷ����Ȩ���ݡ����ǣ���ʵ���л��̼����������أ��������ȵظ��̸�����������ǰ�����ٿ����˲������������Σ�ֻ������취�����ݽ���ծ��·��½���йɷֻ����ݡ���֮���ر�ǿ��������ծ������IJ���ͬ��·�������·Ȩ�����ڱˣ�����ծ��·Ȩ�������ҡ�����ָ��������ר����ɣ�һ�����£�����ת�˱�е���½�ڵ��ѣ�����ǿ�߲�ת������������������Ϊ�����ֻ���³��ܰ���·Ȩ��ʧ���������ס��ߣ��������·����Ȼ���£�ծȨ�����ø�Ԥ·���³����桱�ࡣ��֮��ά��������·��Ȩ��˼�룬���ջ�������·����Ȩ�����ϱ�¶�ø���������������ʮ���꣨1900�꣩����·��ʢ���������������˹�˾��Լ���ɸù�˾��������·����������ΥԼ����˾��Ʊ������֮һ��������ʱ���˾���������桢����ʡ���̵�ǿ�ҷ��ԣ�Ҫ��������Լ���ջ��죬������Ȩ����֮��ȫ��֧����ʡ���̣���Ϊ���˾ٹ�ϵ����·���������Ȩ��Ȩ�����ڱسɡ��١�������������������·��������ȹ��а죬���÷��Ȩ��������«����·������ˣ�����·�ٹ�ȷ���������������������·Ȩ���亦����˼�顱�ڡ��������ˣ��ָĻ��ַ��������Ħ����˾������˹�˾���ޣ���������֮���ܾ����������Է���ǰԼ��������Ϊ�ǣ����������������������ϰ���϶ϲ��ɡ��ۡ�ʢ����ƫ̻������������������֮����Ȼ���Ʋ��ʢ�����������¶ϲ�������ʢ�����족�������µԺ�ĵ籨��˵������֮�n�n������ȴ�ߣ���Ϊ��ʡ����Ȩ������������֮���±ִ������������ѣ��ص��׳�������ջ���Ȩ��������̻���߲����ţ������֦�ڣ���ʡ�������ܡ�����֮����ǿ��Ҫ���£����͡����������֮��������һ�־�����ʢ��������Ԥ���£����ݣ��������̸�У����Ը߰������ջ�����·Ȩ��
��������������֮������ά���й���Ȩ��̬���Ǽ���ģ���ʩ�ǻ����ģ��ر�������չ���幤��ҵ�Ե�����������룬��ʾ������������˾��õı���֮·����ʵ����Ҳȷʵ�յ���������֮�����ij�Ч����������������֯ҵΪ�����ݵ�ʱ���أ�����֯���ֲ�Ʒ�����������Ĵ���ʡ������ȡ�����ȿֺ٣���֮�������ڡ�Ȱѧƪ����Ҳ�����Ժ���˵��������ɴ��Ϊ����˿ڵ�һ���ڣ���Ƽ���ǧ���������Ժ�����֯����������ÿ�꺺�ڽ���֮���ѽ���������ʮ����ƥ���ڡ�
������Ȼ�����ڵ�ʱ�й���ֳ��ؾ�����̬���Գ��ͣ���֮�����˲�����������������ʱ����й���Ȩ�Ӷ�Ķ������е��ף���������֮�����ij�Ч�����������ʱ����й�����ľ��ģ���ԣ�Ҳʮ�ֿ�������֮��֮��������ʶ�����ȱ�ޣ���δ���������ʡ�������Ȩ�ŵ������ľ��ÿ�ѧ��ȫ�̽�����ȥ���ǣ�һ����������ʵ����������ʵ���ʽ��ȱ�����������������ؽ�����������Ϊ������������Ҫ�����������ֱ�Ȼ���൱�̶������й���Ȩ�����ְ�ֳ�����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