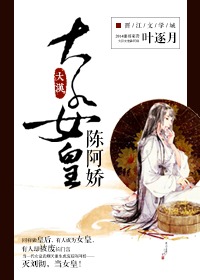放啸大汉-第1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百七十九章 【都护换人了】
青琰、阿离、韩氏兄弟等人刚离开,又来一队老熟人,为首二人,正是杜勋与丘仲。而他们身后的几个扈从,也是曾随军西征的都护府吏士。
初六、阿罴、宗巴与杜勋、丘仲都是老熟人了,都惊喜相迎。
张放走出草庐,笑问:“升赏可下来了?升什么官?”
杜勋嘿嘿一笑,见牙不见眼,一揖到底:“托公子的福,老杜现在是交河壁的假司马。”
“可喜可贺。”张放连连拱手,真心为杜勋欢喜。
交河壁最高指挥官是戊已校尉,左右手就是军司马与校尉丞,接下来就是假司马。遥想一年多前,杜勋不过区区一个队率,低级军官。如此之短的时间,蹿升为六百石的假司马,挤身高级军官。果然是“因功授爵,非功不侯”啊。
丘仲也按捺不住开心,不等张放询问,自动汇报:“我现在是队率了,武爵升至七级千夫。”
张放含笑点头:“很好,你阿父也会为你骄傲的。”
说到其父丘堂,丘仲更为感激,若不是张放暗中出力,他父亲被关押下去,就算不死也得残废。
在一片感谢声中,张放振声笑道:“甘君、陈君,最应当感谢的二位缘何跚跚来迟啊!”
山道传来一阵豪笑,正是甘延寿特有的洪钟大嗓:“我等居功,少侯受累,实在无颜以对!”
随着话语声,山道转弯处现出甘延寿、陈汤的身影。张放趋前相迎,这两人现在一个是列侯,一个是关内侯,就身份而言,都不在他之下了。虽然里子还差得很远,但双方再见,已可施平礼。
双方见礼之后,相视而笑,仿佛又回到当初征尘万里的时光。
甘、陈二人让杜勋等扈从摆好牺牲祭品,向张氏祖陵拜祭。
初六等人也在草庐前摆好三张白苇席与三张短案,案上没有酒肉,只有桃花饮。这是在三月桃花盛开时,摘取花瓣,晾晒干后储藏。用时以沸水冲之,可得溢满桃花芬芳的饮品。三月饮桃,九月饮菊,在汉代很普遍,算是古代自制饮料。
三人落坐,张放举杯,对甘、陈道:“祝二位心愿达成,功成名就。”
陈汤饮毕,放下耳杯,感慨不已:“惭愧,若无少君出力,我等恐怕也无法立身此地。汤昔年有负缪侯举荐之恩,今又承少君如此大恩……汤欠富平侯之恩德,此生不知何以为报。”
甘延寿也道:“少君助力,满朝不知,若非杜勋说起,谁能想到说服刘子政出面的竟是少君。如此大恩,延寿及西征将士,感铭五内。”
张放顿杯于案,正色道:“这是二位应得的荣耀。若是远征万里,披肝沥胆,斩王灭胡,扬汉家天威,返朝却落得身陷囹囵的下场,岂不寒了天下人之心?”
甘、陈感动之余,深为当初让这位富平少侯一同西征的决定而庆幸不已。
张放问道:“二位调任北军,何时上任?”
甘延寿答:“陛下准我等休沐十日,下月初便需到任。”
张放目光闪动:“不知下一任西域都护及使节是谁?”
陈汤答道:“这人少君认识,而且,住得很近。”
张放微讶,略加思索,心头一动,脱口道:“莫非……是段令段子松?”
陈汤笑道:“然也。”
张放亦笑:“果然是熟人,而且住得够近。”
张放所说的段令,就是杜陵县令段会宗,字子松。身为杜陵令,段会宗本就有为诸侯服丧提供便利及监督之责。段会宗每隔十天半月都要来拜会他,询问所需。
张放早在年初首次服丧时,就认识段会宗了,不过那会的段会宗对他是敬而远之。张放也知道,他那时名声不好,连向儿时好友打听个事都不受待见,所以也无怪罪之意。直到他上疏斩衰,为双亲服丧一年,朝野俱赞,这才挽回名声。而段会宗也在此事之后,渐露善意,一改往日拜会时的敷衍,诚心拜望交谈了。
张放彼时还不知这老段将来在西域的地位,不过见此人年不过三旬便任杜陵令,身强体健,举止沉稳,思路敏捷,跟陈汤很像,便知是个有料的家伙。须知当时西汉长安诸陵相当于帝都卫星城,陵邑所居者非富即贵,豪强众多,没有点背景与手段,根本吃不住。换言之,能安稳坐上这个位置的,都是有两把刷子的。
西域都护一般任期为三年,朝廷按需要召回或留任。甘延寿从建昭二年秋到任,到建昭四年春调职,只当了一年半的都护。这是没法子的事,发生了矫诏这种事,赦罪叙功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哪可能还让你呆在西域都护这个位子上,换人是肯定的。
在甘延寿去职之后,朝廷五府推荐(即三公、太傅和车骑将军等联名推举),以段会宗为下一任西域都护、骑都尉,兼使节。而西征有功的郭习则调任都护府副校尉。
“这是昨日未央诏令。”
“原来如此。”张放微微点头,因为目前处境的缘故,他对朝堂这一块的消息来源还略为滞后。虽然甘延寿被免职颇为遗憾,但对段会宗出任西域都护,张放还是乐见其成的。此人未必有陈汤、甘延寿的进取之心,守成应该没问题。郅支覆亡后,西域将会获得很长时间的安宁,身为西域都护,能守成就好。而最重要的是,有这样一位老熟人出任西域都护,自己的丝路商贸计划就更有把握了。
张放神游万里,对眼前客人却也未失礼数,拱手道:“义成侯,陈侯,将来你我同朝为官,还请多加关照。”
这话得倒过来说吧,甘延寿与陈汤连忙回礼:“正当如此。”
三人正叙话间,三才急趋而至,躬身禀报:“禀家主,杜陵令请见。”
说曹操,曹操到啊。
张放与甘、陈相顾而笑:“想必是这位未来的都护最后一次履责了吧。”
~~~~~~~~~~~~~~~~~~~~~~~~~~~~~~~~~~~~~~~~~~~~~~~
(感谢凤萌、菜猪、小胖、碧海…孤帆、¥我是黑狼¥、无毒无味笑看人生、莫再提莫再讲、月隐清雲、wapv、圣地之烽、、bywfw、水月亮123、荣耀香帅、云朵下的天籁、我的心里住着一只猫、何以钦落、感动……)(未完待续。)
第一百八十章 【陶·瓷】
(感谢凤萌、菜猪及诸位打赏投票的书友,这股洪荒之力,我看着都怕怕……)
~~~~~~~~~~~~~~~~~~~~~~~~~~~~~~~~~~~~~~~~~~~~
张放交待的各项事宜,交令最快的是渠良。渠良接受的命令是两条,考察侯府名下工坊里的造纸与制陶流程,然后回报。
由于是首次接受家主之令,家令张敬臣不敢把收购纸坊的事交给下人,而是亲自操刀,多方考量,慎之又慎,生怕不能令家主满意。如此一时半会渠良也没法考察造纸,便先汇报制陶之事。
渠良做事很稳,他不光一人来,还带了一位制陶三十多年的老匠人同行,以备咨询。
陶匠名田安,年逾五旬,背有些佝偻,一脸褶皱,须发皆白,一双粗黑的手掌,褶皱比脸上还多。田安所在的陶坊,就在长安城廓西南,各种工坊遍布。
田安曾在老家主出殡时远远见过少主一面,如今竟能近前拜见,着实惶恐,一直伏身,头都不敢抬。
张放先是详细询问渠良,问得差不多之后,再转向老陶匠,语气平和:“田匠,听说你制器已有三十余载?”
田安伏身慌忙回应:“回家主的话,老奴从爱侯时期就在坊里制陶,已有三十六载。”
爱侯是曾祖张延寿的谥号,也就是说。这田安早在张放曾祖时期,就开始制陶,果然是老匠。
张放微笑:“既是老匠,这制陶的手艺,想必很娴熟吧?”
说到手艺,田安惶恐之中,亦不免有一丝自得:“老奴这手活,不敢比长安大匠,但在直城门以西,咱陶坊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张放问起制陶流程,田安起先还有点嗑巴,后面越说越流利,甚至脸上都涌起一种神采。
张放安静听着,基本不打断,过程中还不断点头、微笑。他的肯定令田安更加进入状态,连声音都高昂起来。
张放以前休闲时也玩过陶艺,对古代制陶略有了解,不过也是泛泛。此时听到老匠人连比带说,从最开始的淘泥,到摞泥、拉坯、印坯、修坯、捺水,以及画坯、上釉,最后入窑烧制。整个过程所需时日,注意事项,手艺关窍,清楚明白。
张放一边仔细听着,一边看着手里一个酱褐色的黑瓷碗。这种黑瓷碗准确的称呼是釉面陶,属于原始瓷器,似瓷而非瓷。器物内壁施一层薄釉,外壁只在口沿及肩上部施釉,腹中部和下部露胎,显得十分粗陋。
秦汉以来,这种釉面陶成为富人家用器皿主流,民间仍多用陶器。富平侯府的产业,自然是走高端路线,制作出售的多为釉面陶。
张放摇摇头:“这些是陶,不是瓷。”
正说得口沫横飞,十分起劲的田安一怔,惊讶望着这年轻的家主,旋即知失礼,浑身哆嗦一下,赶紧伏首,喃喃道:“长安制陶皆如此,家主……”
张放瞥了渠良一眼,前些日子他交待任务后,特意叮嘱一句,让渠良在考察各陶坊时,末了一定要问一句“为何不制青白瓷”。如果有匠人明白,便可带来,若不明白,就一直找下去,直到找到明白人为止。
渠良今日既然带此人来,必定有所得,可是这老匠人的回答,却令张放皱眉——皆如此?那带来干什么?
渠良被少主一瞪,额头也渗出汗来。他这十余日在一位熟识府卫的伴同下,找遍长安西市、外廓、诸陵邑,那句密语一样的“为何不制青白瓷”,问了不下百十遍,几乎无人知其意。最后好不容易找到这个老匠人,竟然听懂了“密语”,渠良当即抓救命稻草一样将他抓来,没想到这老匠头整出这么一句,完了……
张放目光转回老匠人身上,语气依旧平和:“你知晓制青白瓷?”
田安嗫嚅半天,突然嘣出一句:“老奴曾在师祖家中,见过天青色瓷,听师祖所言,是其祖上……”
啥?!师祖?还祖上!哪得是啥年头?你不会告诉我先秦时期就有瓷器了吧!
“……老奴本是会稽乌程人氏,于莫干山下,世代制陶为业。少时为学徒,曾听老匠工言道,先祖师曾为当年越王制秘器,施过一种青釉……”
老匠人田安的述说,为张放揭开了一个千古之迷——最早的釉面陶,竟然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当时吴越制陶业十分发达,大约在越国中晚期时,有匠人研制出一种釉水,施于陶坯表里,经高温烧制,出窑后陶器莹然,呈现墨绿色。这种介于陶与瓷之间的釉器,被当做王室秘器(即殉葬品),葬于越国诸王族与贵族的墓葬中,并未当做生活用品,故而未宣诸于世。
越国灭亡后,因不再制秘器,这门手艺逐渐失传,只在历代莫干山陶匠中口耳相传。
原来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釉面陶瓷了,而越人陶匠,代代相传,有所突破,亦在情理之中。张放按捺激动,问道:“你可曾见过实物?”
田安回道:“少时曾在师祖家见过一件残器,色泽天青,触手温润,与寻常陶器大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