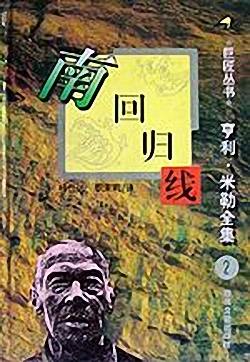北回归线-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又活了一回。我活着,这一回不凭借回忆往事,像我跟别人谈起的那样,不过我
活着。”
信就是这样开头的,没有问候的话,没有日期,没有地址,写在从空白笔记本
上撕下来的格纸上,字写得很轻,字体华丽、潦草。“这就是为什么你同我非常亲
近,不论你喜不喜欢我,在内心深处我倒认为你是恨我的。通过你我知道自己是怎
么死的:我又看到了自己在死去,我快死了。除了死掉拉倒,还有点儿别的。这也
许是我怕见到你的原因——也许你在我身上玩了鬼把戏,然后死了。如今事情发生
得很快。”
我站在石头旁边一行行读过去,这一番关于生死和事情发生得很快的空谈听起
来像疯话。据我所看见的,什么也没有发生,除了报纸头版上登载的那些寻常灾祸
。过去六个月来鲍里斯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躲在一间房租便宜的小屋里,或
许同克朗斯塔特通过心灵感应术保持着联系。他讲到退却的防线和撤出的战区,以
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好像他正在一条战壕里向司令部写报告。也许他坐下写这封信
时穿着常礼服,也许他搓了几回手,以前有顾客上门来租他的公寓时他常常那样。
他又写道,“我想叫你自杀的原因是……”看到这儿我不禁大笑起来,以前在波勒
兹别墅他常把一只手插进常礼服的后襟里踱来踱去,要不就是在克朗斯塔特那儿—
—不拘哪儿,只要有摆下一只桌子的地方就行——同时滔滔不绝地把这番生与死的
废话说个够。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听懂过一个词,不过这场面倒也热闹。作为一个
非犹太人,我自然对一个人脑袋里闪过的各种念头感兴趣。有时他会直挺挺地躺在
沙发上,那是被脑子里涌现的潮水般的念头弄得疲乏了。他的脚刚好碰到书架上,
那儿放着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书,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书对我没有用。我要承认
他把这些书渲染得很有意思,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它们是讲什么的,有时我也会偷偷
翻翻其中一卷,看看那些异想天开的思想是不是真是这些人自己的,因为鲍里斯总
说这些观点是他们的,不过他的话与他们的思想联系不大,基本上不沾边,鲍里斯
有他自己的独特说法,就是说,当我同他单独在一起时,不过一听克朗斯塔特讲话
我就觉得是鲍里斯剽窃了他的高见。他俩谈论的是一种高等数学,不含一点血肉的
东西,鬼魂般荒诞,抽象得可怕。待他们谈到死的事儿时才变得具体一些了。不管
怎样,切肉刀和砍肉斧也得有一个柄。我非常喜欢参加那些讨论,生平第一次觉得
死亡很吸引人,我是指所有带有不流血痛苦的、抽象的死亡。他们不时会因为我还
活着恭维我,但是他们的恭维方式令我很窘迫,他们叫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在十
九世纪并出现返祖现象的遗老、一条浪漫的破布、一个有情感的直立猿人。鲍里斯
尤其从挖苦我中得到乐趣,他要我活着以便自己能随心所欲地死去。他看我、揶榆
我的样子…杀的原因是当时我同你非常亲近,或许是再也不会有的那么亲近。我怕
,我非常怕哪一天你会回来找我、死在我手上,那样一来一想到你,我就会陷入孤
立无援的境地,这是不能忍受的,为此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或许你能想象出他会说这种话!我自己却不清楚他怎么看待我,至少我本人显
然纯粹只是一个观念,一个不吃食物生存下来的观念。鲍里斯向来不大重视吃饭问
题,他企图用观念养活我,每一件事情都是观念,然而,当他打主意要把公寓租出
去时却不忘在卫生间里放一只新脸盆。总之,他不想叫我死在他手上。他写道,“
你必须做我的生命,直到最后。这是你可以接受我对你的看法的唯一办法。如你所
见,因为你同某件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一道捆在我身上了,我想我永远也摆脱不
了你,也不希望这样做。我死了,但我想要你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兴旺。正是因为这
一点,我向别人谈起你时总有点羞愧,这样熟悉地谈论自己总是不容易的。”
也许你会以为他迫不急待地要见我,希望了解我正在做什么。错了,他在信中
连一行也不曾提及具体的或个人的事情,除了这一番有关生死的话,除了这一小段
战壕中写就的话,这一小股向每个人宣告战争仍在继续的毒气。有时我自问为什么
被我吸引的人都是精神错乱的人、神经衰弱的人、神经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尤
其是犹太人。一个健康的非犹太人身上准有某种叫犹太人激动的东西,就像他看到
发酸的黑面包一样。比如说莫尔多夫,据鲍里斯和克朗斯塔特说,他自封为上帝了
,这条小毒蛇毫无疑问在恨我,可他又离不开我。他定期跑来叫我侮辱一顿,对于
他这像吃补药一样。起初我对他确实十分宽宏大度,不管怎样他在付钱叫我听他说
。尽管我从未显出很同情的样子,我却明白涉及到一顿饭和一点儿零花钱时要免开
尊口。
过了不久,我发现他竟是这样一个受虐狂,于是便时时当面嘲弄他。这就像用
鞭子抽他,使悲哀和忧伤伴着新迸发的活力一起涌泻了。也许我们之间一切都会和
谐的,若不是他觉得保护塔尼亚是他的职责。塔尼亚是犹太人,这引出一个道德问
题。他要我忠于克劳德,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个女人我还是一往情深的。
他有时还给我钱,叫我去跟她睡觉,直到他领悟到我只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色鬼
为止。
我提到塔尼亚是因为她刚从俄国回来,几天以前才回来。西尔维斯特仍留在后
面去钻营一份工作,他已完全放弃了文学,又投身于那个新的乌托邦了。塔尼亚要
我同她一起回去,最好回到克里米亚,去开始新的生活。那天我们在卡尔的房间里
大喝了一气酒,商量这件事的可能性。我想知道到了那儿我做什么谋生,比方说,
能不能干校对员。塔尼亚说我不必担心干什么,只要我真心愿意去他们会替我找到
一份工作的。我想显出热心的样子,结果却显得悲戚戚的。在俄国,人们可不想看
到哭丧的脸,他们要你快活、热情、轻松、乐观,听起来那儿同美国一样。可我天
生就缺乏这份热情,当然我没有对她说,可我暗自希望他们扔下我,让我回到自己
的小职位上去,呆在那儿,直到战争爆发。这一套关于俄国的骗局略略使我有些不
安,塔尼亚为此却很动感情,因而我们几个喝光了十几瓶便宜的红葡萄酒。卡尔像
蟑螂一样蹦来蹦去,他身上的犹太血统足以使他因为俄国这样一个念头而欣喜若狂
。除了叫我们结婚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立即结婚。他说,“结婚吧!你们不会损
失什么!”然后他假装要去办一件小事,好叫我俩来个速战速决。塔尼亚也想干,
可是俄国的事已牢牢地移植在她脑子里了,她便在对我唠叨中浪费完了这段时间,
她的话使我有点恼火和不安。可我们必须考虑吃饭、去办公室了,于是我们在埃德
加一基内林荫道上挤进一部出租车飞速驶走了,这儿距公墓很近。这时正是坐在敞
篷汽车上穿过巴黎的好时辰,葡萄酒在肚子里翻来滚去更叫人觉得格外痛快。卡尔
坐在我们对面的折叠座位上,脸红得像一棵甜菜。这个可怜的狗东西倒挺快活,想
到他将在欧洲另一边过一种美妙的新生活了,同时他也有点儿怅然,这我看得出来
。他并不真想离开巴黎,正如我也不想离开一样。巴黎对他并不好,同样,它对我
、对任何人都不好,可是当你在这儿饱经磨难之后仍是巴黎使你留连忘返,你可以
说它掌握住你了。它像一个害相思病的婊子,宁愿死也要拽着你。我看得出,他就
是这样看待巴黎的。过塞纳河时他咧着嘴傻笑,四下里望望建筑物和塑像,仿佛是
在梦中看到它们。对于我这也像一场梦,我把手伸进塔尼亚的胸口,拼命捏她的奶
头,我留意到桥下的流水和驳船,还有圣母院,正像明信片上画的。我醉醺醺地自
忖一个女人就是这样被奸污的,不过我仍很滑头,知道拿俄国、天堂或天下任何东
西换我脑子里这些乱糟糟的念头我都不会换的。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独自在胡
思乱想,很快我们就要把很多吃的塞进肚子,还有额外叫的一切好吃的、一些会淹
没去俄国这件事情的上好浓甜酒。有了塔尼亚这样一个充满朝气的女人,他们一旦
想到什么才不会管你怎样呢。放手让他们干,他们会在出租车上就扯下你的裤子。
不过穿过街上来往的车辆还是很妙的,我们脸上涂着胭脂,肚子里的酒像阴沟一样
发出汩汩的响声,尤其在我们猛地拐入拉菲特街之后。这条街的宽度恰好能容纳街
尾那所小殿堂,上面是耶稣圣心,一座有外国情调、乱七八糟的建筑,这也是穿越
你的醉酒状态、丢下你无助地在过去的日子里游泳的清晰明白的法国观念,这就是
叫你在完全清醒而又不刺激神经的飘忽不定的梦幻中游泳。
塔尼亚回来了、我有了稳定的工作、关于俄国的醉话、夜晚步行回家、盛夏的
巴黎——生活似乎又昂起头来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鲍里斯寄来的那类信令我觉得
十分荒诞的原因。我几乎每天都在五点左右同塔尼亚会面,跟她一起喝一杯波尔图
葡萄酒,她把这种酒叫作波尔图葡萄酒。我让她带我去以前从未到过的地方,去香
榭丽舍大街附近的时髦酒吧,那儿的爵士乐声和姑娘低声吟唱声仿佛渗透进桃花心
木的家具里去了。即使是去上厕所,这软绵绵的伤感旋律也在身边索绕,它通过排
气扇飘进厕所,使生活变成虚幻,变成彩虹色的泡沫。不知是因为西尔维斯特不在
还是出于别的原因,塔尼亚现在觉得自由了,她的一举一动简直像天使一样。有一
天她说,“我走之前你对我很不像样。你干吗要那样做?我从来没有做过伤害你的
事,对吗?”我们在柔和的灯光照射下,在渗透那个地方的软绵绵餐室音乐声中变
得易动感情了。快要到去上班的时间了,我们还没有吃饭,支票簿存根摊在我们面
前——六法郎、四个半法郎、七法郎、两个半法郎——我机械地数着,同时在想自
己会不会更乐意去当一个酒吧招待员。常常是这样——塔尼亚跟我说话,当她滔滔
不绝地谈到俄国、未来、爱情这一类废话时,我会想到最不相干的事情上去,想到
擦皮鞋、当厕所服务员。我尤其想到这个,因为她拉我去的那些下流场所很舒适,
我从来不曾悟到我去的那些下流场所很舒适,我从来不曾悟到我会非常理智,也许
会老、会驼背……不,我始终在想,未来不管怎样合情合理仍会处在这种环境中,
同样的乐曲会灌进我脑子,酒杯碰在一起,每一个形状姣好的屁股后面会放出一道
一码宽的香气,足以驱散生活中发出的臭气,甚至楼下厕所里的臭气。
奇怪的是这个想法从未阻止我同塔尼亚踊跳到这些时髦酒吧里去。离开她当然
是容易的,我常常领她来到办公室附近一所教堂的门廊上。我们站在黑暗中最后拥
抱一回,她对我低声道,“老天,现在我该干什么?”她希望我扔掉工作,这样就
可以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