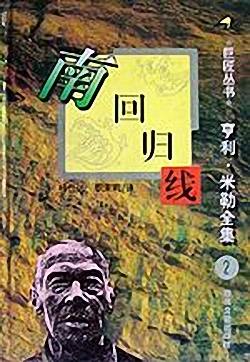北回归线-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容易的,我常常领她来到办公室附近一所教堂的门廊上。我们站在黑暗中最后拥
抱一回,她对我低声道,“老天,现在我该干什么?”她希望我扔掉工作,这样就
可以白天黑夜都同她做爱。她甚至不再去理会俄国了,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行。可是
我一离开她头脑就清醒了。从旋转门里进去后我听到的是另一种音乐,不那么缠绵
,不过也很好听。香气也成了另外一种,不止一码宽,却无处不在,像是汗味和机
器散发出的薄荷味。进门时我通常都喝得大醉,一进来便好像突然来到了海拔低的
地方。我一般是一进来便直奔厕所,它使我振作起来。厕所里凉快些,要不就是流
水声造成了这种错觉,厕所始终是一种冷灌洗疗法,而且是真正的。进去之前你必
须经过一排正在脱衣服的法国人。哼!这些魔鬼身上发出了臭味,为此他们还拿高
薪呢。他们站在那儿,脱掉了衣服,有的穿着长内衣、有些留着胡子,大多数人皮
肤苍白,像血管中有铅的瘦老鼠。在厕所里你可以仔细看看他们无所事事时都想些
什么,墙上涂满了图画和文字,都是诙谐可笑的猥亵玩艺儿,很容易看懂,总的来
说挺好玩、引人喜爱。要在某些地方涂写准还需要一只梯子,我想,即使是从心理
学角度来看这样做也是值得的。
有时我站在那儿撒尿,不禁想这些乱涂乱抹的东西会给那些时髦女人留下怎样
的印象,我在香榭里舍大街看见她们进漂亮的厕所。如果她们能看到在这儿人们怎
样看待一个屁股,不知道还会不会把屁股撅得那么高。在她们周围,无疑一切都是
薄纱和天鹅绒的,要不就是她们从你身边赛卒走过时身上发出的好闻气味使你这样
想。她们中有些人起初并不是高贵淑女,有些人摇头摆尾地走路只是在替她们的行
当做广告。当她们独自呆着时,在自己的闺房里大声谈话时,也许口中也会说出一
些奇怪的事情,因为她们所处的世界同每一个地方一样,发生的事情多半是屎尿垃
圾,同任何一个垃圾桶一样脏,只是她们有幸能盖上桶盖。
我说过,同塔尼亚一起度过的下午对我从未有过不好的影响,有时我喝酒喝得
太多,只得把手指伸进喉咙里——因为看清样时不清醒是不行的。看出哪儿漏了一
个逗点比复述尼采的哲学更需要精神集中。有时喝醉了你也可以很精明,可是在校
对部精明是不合时宜的。日期、分数、分号——这些才是要紧的,而头脑发烧时这
些东西是最难盯住的。我不时出些荒谬的错,若不是早就学会了如何舔老板的屁股
,我准早就被解雇了。
有一天我还接到楼上那个大人物的一封信,这个家伙高高在上,我甚至从来没
有见过他。信上有几句挖苦我具有超凡智力的话,言辞间他明白无误地暗示我最好
本分些、尽职尽责,否则会受到应有惩处的。老实说,这把我吓得屁滚尿流,从此
说话时再也不敢用多音节的词了,实际上我一夜几乎都不开口。我扮演了一个高级
白痴的角色,这正是他们所要求的。为了奉承老板,我不时走到他面前礼貌地问他
这个或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他喜欢我这一手,这家伙是个活字典、活时间表,不论
他在工间休息时灌了多少啤酒,在某个日期或某个词的词义上你永远也难不倒他。
而且他的工间休息时间全由他自个儿掌握,因为他要巡视自己主管的这个部门,他
天生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唯一叫我懊悔的是我懂的太多,尽管我很小心谨慎还是不
免暴露出来。
假如我来上班时胳膊底下夹着一本书,我们这位老板准会看见,若是本好书他
便会怨恨我。不过我从来没有有意做什么事情使他不快,我大喜欢这份工作了,绝
不会把绞索往自己脖子上套。
同一个与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交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即使只用单音节的词
也会露馅。这个老板心里明白我对他讲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然而不知道为什么,
他非常喜欢驱走我的迷梦,并给我灌输各种日期和历史事件。我想,这就是他报复
我的方法吧。
结果我患了轻度神经官能症,一吸进新鲜空气便信口胡说。
清早我们回蒙帕纳斯时,不论谈到的是什么话题,我都要尽快用消防水龙头往
上面浇水,打断这个话题,以便让自己从变态的梦幻中解脱出来。我最喜欢谈谁也
不懂的事情,我已经患了一种轻微的精神错乱,我想这种病叫作“模仿言语症”。
一夜间校对的文稿标签都在我的舌尖上跳舞,达尔马提亚——我曾拿到为这个美
丽的珠宝胜地做的广告。对了,达尔马提亚,你坐上火车,早上毛孔便出汗,葡萄
绷破了皮。我能从这条壮观的林荫大道一直滔滔不绝地谈论达尔马提亚,一路谈到
马萨林红衣主教的宫殿,只要我愿意还可以说下去。我连它在地图上的位置都搞不
清楚,也从来不想搞清。可是在凌晨三点你身体疲乏不堪、衣服被汗水和广藿香浸
透,手镯叮当响着从绞衣机里通过,这时伙伴们要我说的那些喝醉了啤酒后胡扯的
事情都毫无意义——那些地理、服装,演讲、建筑之类的琐事。达尔马提亚是要在
夜里某个时辰谈论的,那时交通警的锣已不响了,卢浮宫的庭院显得又美妙又荒谬
可笑,使你想无缘无故地哭一场,这正是因为周围又美丽又静谧,那么空旷,与报
纸头版和楼上掷骰子的人全然不一样。有达尔马提亚像一把冰冷的刀锋搁在颤动不
已的神经上,我才得以体会途中那些最美妙的感觉。
好笑的是我可以走遍全球,可是总想不到要去美国,对于我它比一块消失的大
陆更浩渺、更遥远,我对消失的大陆尚存有某种神秘的向往,对美国却毫无感情。
有时我也确曾思念莫娜,不是把她当作特定时间空间中的一个人去思念,而是抽象
地、超然地思念,仿佛她已变成一大团云彩状的东西冉冉升到空中,这团东西遮住
了过去。我不能使自己长时间地思念她,不然我就会从桥上跳下去的。真怪,我已
对这种没有她在身边的生活习以为常了,但是只要想她一会儿便足以完全破坏我的
满足,把我又推向悲惨的过去那个令人痛苦的阴沟里。
七年来我不分昼夜四处游荡,心里始终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她。若是有一位
基督徒像我忠于莫娜那样忠于上帝,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早已成为耶稣基督了。我昼
夜思念着她,甚至哄骗她时也是如此。有时,正在做其他事情,觉得自己完全忘却
了这件事情时——也许正在拐过一个街角——我眼前会突然出现一个小广场几棵树
和一只长椅,在这僻静的地方我们站着争吵,在这儿我们用刻薄的语言、争风吃醋
的话题吵得对方发疯。我们总是拣一个僻静的地方,比方说吊刑广场清真寺外昏暗
悲哀的街道,或是布尔特伊大道那个敞开的墓穴一带,那儿一到晚上十点钟便死一
般寂静,使人联想到谋杀、自杀或任何可以创造人类戏剧遗迹的东西。当我意识到
她走了,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便打开了,我觉得自己在下跌、下跌
,跌进幽深的空间中去。这比流泪还糟,比懊悔、创伤或悲哀更深刻,这是魔鬼撒
旦被抛入的无底深渊,无法再爬上来,没有光线,没有人说话的声音,没有人手的
触碰。
夜晚穿过街道时我曾几千次想她回到我身边的一天会不会到来,我将渴望的目
光全投向建筑物和雕像,我那么渴求、那么绝望地望着它们,到此时我的思想准已
同这些建筑物和雕像融为一体了,它们一定浸透了我的痛苦。我也忍不住忆起我们
肩并肩穿过这些现在浸透着我的梦想和渴望的悲哀、幽暗的街道时她什么也没有注
意到,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对于她这些街道同其他街道是一样的,只是略微脏一点
儿,仅此而已。她不会记得在某一个角落我曾驻足捡起她的发夹,或是我俯身替她
系鞋带时标明了她落脚的地方,它将会永远留在那儿,甚至在大教堂被毁坏、整个
拉丁文明都永远被消灭后它仍将留在那儿。
一天夜里沿着勒蒙街散步时一阵不寻常的痛苦和忧伤攫住了我,一些事情栩栩
如生地展示在我面前。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因为我常常闷闷不乐地、绝望地在这条街
上行走,还是因为我想起了一天夜里我们站在吕西安一埃广场时她说过的一句话。
她说,“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看你写过的那个巴黎?”想起这话时我明白了,
我忽然悟到根本不可能指给她看那个我已经了解的巴黎,那个区域未确定的巴黎,
那个只是由于我的孤独和对她的渴求才存在的巴黎。这样一个巨大的巴黎!再探究
它一遍会花去一个人的一生。只有我拥有打开它的钥匙,这个巴黎不适合游览,即
使是抱着最好的意愿来旅游,只能在这个巴黎生活,每天必须体验它的一千种不同
的折磨。这个巴黎像一个恶性肿瘤在你体内长大,越长越大,直到吞噬掉你。
跌跌撞撞地走过沐佛塔尔街,这些往事在脑子里转来转去,我又回想起以往的
另一件怪事。那是一本导游手册,莫娜要我替她翻书页,因为封面太沉重,可我当
时发现根本无法翻开。一点原因也没有,只是因为那时我一门心思都去想沙拉文,
现在我正是在他的神圣管区内漫游——仍是一点儿原因也没有——我忆起有一天受
到日复一日经过的那块招牌启发后我冲动地闯进奥尔菲拉公寓要求看看斯特林堡曾
住过的房间。截至那时为止我还没有遇到很大不幸,尽管我已失去了所有的东西,
也已尝过空着肚子在街上徘徊、提心吊胆地提防警察的滋味。那时我在巴黎还没有
交上一个朋友,这种状况与其说令人沮丧倒不如说是使人茫然,不论我在这个世界
上流浪到何处,最容易找到的莫过于一个朋友。不过实际上迄今为止我还没有遭遇
什么太大的不幸,一个人的生活中可以没有朋友,正如他没有爱情甚至没有钱也可
以生活下去,尽管人们认为钱是必不可少的。我发现,一个人可以只凭悲哀和痛苦
在巴黎生活!这是一种苦涩的滋养品,或许对于某些人这是最好的滋养品。不管怎
样,我还没有落到穷途末路的地步,我只是在同灾祸调情而已。我有充裕的时间,
有闲情逸致去窥探别人的生活,去同已死去的传奇故事闹着玩。不论一件事物有多
么肮脏,一旦塞进一本书里便显得令人惬意地遥远和陌生了。离开这个地方时我意
识到自己唇边浮现出一丝讥讽的笑容,好像在对自己说,“别着急,奥尔菲拉公寓
!”
从那时起我当然明白在巴黎的每个疯子早晚都会发现一件事:并不存在为受磨
难者预备的现成地狱。
现在我好像有点儿明白她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斯特林堡的作品了,我看到她读完
“有味道”的一段后抬起头来,眼睛里充满笑出来的泪水,她说,“你同他一样疯
……你该受罚!”当她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受虐狂后,这位施虐狂是多么高兴啊!她
还没咬自己,看看牙齿是否锋利。我刚刚认识她的那些日子里她浑身都是斯特林堡
的味道,使我们聚到一起的是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