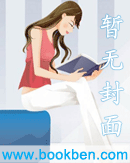应是屐齿印苍苔-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定,有条不紊地肆应忙碌。如果说鲁迅的溘逝对芸芸众生是星陨,那么对她
个人无疑是天崩;但她的神情却使人相信,即使天真的塌下来,她也能用双
肩顶住。
抗日战争的垂天战云,对她是重大的磨练。她在息影十年之后,又像被
称为“害马”的学生时代一样,走上十字街头。她参加的战斗团体,公开的,
秘密的,上层的,下层的,几乎包罗了政治、文化、群众、妇女各个领域。
就我所知,就有如下这一些:以何香凝为首的抗日救国后援会(何香凝被法
租界驱逐出境,退走香港之后,她是留守的三个骨干之一),以胡愈之、郑
振铎等为核心的复社,有孙冶芳、何封等参加的读书会,由教育、宗教界如
沈体兰、吴耀宗等上层人士组成的聚餐会(常在觉林吃素餐,请来自延安的
刘少文等分析形势,传达党的政策),有张宗麟、李平心等数十人参加的地
下国民会议,茅丽英主持的妇女俱乐部(后来茅丽英被敌伪暗杀,群众为她
举行追悼会,景宋先生不顾情势的险恶,不顾朋友们的劝告,毅然赶去参加
了。这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参加杨杏佛追悼会的动人事迹),《上海
妇女》杂志(后来受到压迫,改为《上海妇女知识丛刊》,假托香港出版),
中华女子职业学校(王任叔和她先后担任校长)等等。她带着羸弱多病的海
婴到处奔走,募款、卖国旗徽章、义卖手工艺品、办难民收容所,直至组织
新四军慰劳团? 。活动范围的方广与纵深,正是测量她热情高度的标尺。但
这也就给她招来了灾难,给了她一场生死荣辱、大节攸关的严酷考验。太平
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租界不到一星期,不遑喘息,就迫不及待
地逮捕了她。攻坚战必需首先炸开突破口,日本宪兵队的战略意图正是如
此:征服了她,也就掌握了上海人民抗日阵线的锁钥。何况她又是鲁迅夫人,
抓住了她,就可以打开撒向文艺界的网罗。黩武主义和霸权主义必然导致人
类公认的道德的澌灭,日本人民是尊重女性和彬彬有礼的,看看日本宪兵队
如何对待一位手无寸铁而社会知名的妇女,却真是令人怒不可遏,并代他们
感到羞耻。但暴力侵凌,一定要碰在人类尊严和民族尊严的坚壁上,景宋先
生就以零丁弱质而战胜了敌人的凌辱胁诱,酷刑峻法。“身体可以死去,灵
魂却要健康地活着”;“牺牲自己,保全别人;牺牲个人,保全团体”。这
就是她神圣的信条。无怪当时蛰居上海的郑西谛先生,对她以“自己的生命
来保障无数朋友们和同道者的生命与安全”这一点,致以如此热烈的尊崇与
感激。
景宋先生始终如一,殚心罄力以赴的,是鲁迅著作的整理、辑集、出版,
鲁迅手迹、书信、藏书、遗物的搜集保存。刀兵的威胁,政治的桎梏,关山
的阻隔,人事的参商,在在满布困厄,需要煞费经营,才能免于陨越。在四
面荆榛、鬼蜮横行的上海“孤岛”,《鲁迅全集》、《三十年集》的先后问
世,恰如在危城中矗立起耸天的丰碑,特别地引人注目。这是党一力支持,
进步文化界同心协作的结果,景宋先生当然是出力最多的。《鲁迅日记》首
先在《文汇报》晚刊头版专栏地位连续发表,也是“孤岛”文化界的一件大
事,景宋先生亲手从原件中细心移录,工整谨饬,一笔不苟。可惜因为《文
汇报》被迫停刊,连载因此中断。后来《鲁迅日记》原件,竟在她被捕落入
日本宪兵之手,取回的时候,不幸失去了整整一年的日记。否则原件虽遭损
失,发表稿还可以保存全璧。这真是莫大的遗憾。由此可见景宋先生任务的
艰巨,而她对鲁迅遗泽的保卫,却真正做到了地老天荒,海枯石烂,锲而不
舍,直至力竭而仆。这当然出于她满腔燃烧的挚爱与赤忱,更重要的,是出
于公心而不是囿于私衷,因为鲁迅是人民的鲁迅,这是很值得人们和后世感
谢的!
1968 年春,景宋先生因心脏病突发而猝然逝去,是由于戚本禹劫取鲁迅
书信手稿而诱发的。她发了病,送到医院,医院不收,因为在“文化大革命”
中,干部保健制度被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认为是“城市老爷卫生部”,
加以摧毁,景宋先生以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也不能幸免于临危被摈于医
院门外的厄运,等到办好手续,已经无法抢救了。她去世时,江青假惺惺地
说:“是我们没有对她保护好。”但后来查明,鲁迅书信手稿就藏在江青的
保密室里,原来谋杀者正是江青。大家看看这只两脚兽的真实嘴脸吧!
这种情况,我是事后才知道的。景宋先生逝世的时候,我正关在监狱里,
有一天看报,才在报上小小的一角发现了这消息。我放下报纸,长时间沉浸
在默默的悲痛与忧伤中,——这是真正的默哀,因为无可告语。我心想,应
该打个唁电,但这只是在一闪念间。在监狱里想打电报,正与骆驼穿针孔同
其荒诞。古时候没有钟表,人们以分寸计量时间,有所谓“寸阴”“分阴”
的说法,在监狱里蹲久了,我才亲身体会到它的意义。除了阴雨,阳光每天
上下午两次,分东西方向通过铁窗投射进来,窄窄的一小方块,在墙上和地
上,从相反方向缓缓移过,又移出铁窗外去,人的确可以清楚地看出时间的
脚步一分一寸地移动。在监狱里看到阳光,这当然是很大的奢侈,但被囚者
因此也就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一分一寸白白地消蚀,对珍惜生命意义
的人,这真是第一等残酷的刑罚!在这种处境下,人常常会逃向过去,用咀
嚼回忆来填补现实的空虚,有如动物反刍,缅想亲友的音容笑貌,并悬惴将
来劫后重逢的愉快,也就是聊以遣愁的一法。景宋先生是我可以无所顾忌地
谈谈的少数熟人之一,但从此我再也看不到她了。
已经记不起是哪一年了,我笔记本上偶然留下的日期,是2 月21 日,
我到北京景山东前街景宋先生的寓所相访,闲谈了很久,谈得最多的是上海
“孤岛”和沦陷时期的旧事,这使我对她当时的境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临走
时我向她借了一本《遭难前后》,准备重读。她说她只有这一本了,再三叮
咛不要丢失。经过十年浩劫,幸而原书无恙,而物在人亡,我只好把它送还
了海婴。现在此书再度问世,或者可以告慰逝者于地下吧。——也许会有人
发生疑问,在中日友好的蜜月时期,这是否不合时宜?我认为这是多余的周
到。历史就是历史,日本人民是明智和现实的,不像我们有些人那么神经过
敏。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不只是中国人民,东南亚各国人民,还有日本
人民。在这一点上,世界人民是休戚与共、痛痒相关的。广岛的原子弹受害
者,日本人民至今在为他们举行纪念,这并未妨碍美日两国的友好。在美国
和日本的文艺作品中,也从不避忌曾经发生的硝烟血污。光是握手和微笑,
并不能建立真正的友谊。共同的利害关系,和平愿望,人类的道义精神,过
去的历史教训,综合起来,才是友谊可靠的韧带。我个人曾两次进日本宪兵
队,但这丝毫无损于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无损于我对日本这个伟大有
为的民族的钦佩。但过去两个邻邦兵戎相见的不幸事实,却应当永远引为前
车之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的诗句,正是中日人
民世代友好,绵延不断的预言。
1980 年8 月18 日,病中
文品与人品 ——《雕塑家传奇》序
我曾经以为,文品总是人品的表现,因为文艺是心灵工厂的产品,不可
避免地要漏泄灵魂的秘密。——不管是袒露的或潜藏的,甚至带着各种藻饰
的。
徐开垒同志的《雕塑家传奇》,给这种观点提供了正面的例证。我们从
这里看到了作者的爱和憎,欢乐和哀愁,美好的愿望和理想:一颗正直和质
朴的心。
《雕塑家传奇》中包含的篇什,经历了绵长的岁月:沧海翻腾,大地震
颤,世代更新的四十年。它不是历史,却打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它是人民的心电图,想人民所想,感人民所感。
文字是流利而亲切的,有村姑式的妩媚。披阅这些散文,给读者一种感
觉:仿佛在秋天宁静的午后,坐在时间的长河边,四野无人,谛听它在阳光
下淙淙细语,诉说它的沧桑变革。或者在乡村的小客店里,就着青荧的灯火,
面对一位娓娓而谈的人生旅客,东山西海,叙述许多动人的见闻。或者在熙
来攘往的大道边,听一位命运的歌手,用舒徐婉转的调子,演唱生活的颂歌。
为文也真如为人,冷暖甘苦,唯有自知。开垒在《散文随想》(代跋)
里,总结了一个“我”字,楬橥作家不要在作品里回避自己。这可以算是一
种艰辛的参悟吧。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阐述,词中有“无我之境”,有“有我之境”。
严格说来,这并不确切。物是客观存在,思想感情的波动是主观的,物我之
间,无论是由物传人,由人状物,既出之以发自肺腑的灵感,流自腕底的笔
墨,物虽同一,人有万殊,如何能不着主观色彩?“风格就是人”;还是马
克思引用过的、蒲丰的话说得好。
文艺作品中也不乏顾影自怜、自我吹嘘、自我膨胀,乃至“妆罢低声问
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一类的东西,那是另一回事,它只能是作者卑下情
操有意无意的外烁。
“四人帮”为了践踏作家,故意抹煞精神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不同性质,
说:“写文章为什么要署名?看哪个工人在自己的产品上署过名?”这大概
也算是一种高姿态,用以证明“唯我独‘左’”。他们以为有了政治权力,
也就有了胡说八道的权利,这种笑柄,不过是其中的一例。
开垒还从反面总结了两个字:“拘谨”。这是他对自己部分作品的考语。
我想这恐怕正是他的个性在纸上的反映,因为他原是个拘谨的人。
在这一点上,为人与为文应该有些区别。创作必须忠于现实,但观察要
深些,表现手段要丰富些,不能太“老实”——当然绝对不要扭捏作态。
人应当有品,文也应当有品。文字形成个性的过程是艰苦的,但更艰苦
的是个性的突破,从统一中追求多样,从纯净中追求多采。
我和开垒,作为文字之交,也已有40 年之久。起先是我编刊物,他写
稿;后来是他编刊物,我投稿。在崎岖多变的世路中,细水长流40 年,无
疑是弥足珍贵的了。但真要对他的作品作一些不偏不倚、洞中肯綮的分析,
我依然自愧无能。野人献芹,我这些多余的话,如果还有些许可供采择,那
我就将感到喜出望外了。
1981 年4 月4 日,病中
舞台因缘六十年 ——《李健吾剧作选》序
一
“? 。我依旧写我的戏,在一种相当的寂寞里。”
这是李健吾同志在《梁允达》一书序文里的话。其时是1934 年,距今
已将半个世纪。如果从他发表处女作独幕剧《工人》——1924 年算起(那时
他还是个中学生);或者更早一些,从他第一次粉墨登台,在《幽兰女士》
里扮演小丫头那一年——1920 年算起(那时他还是个小学生),那就已经超
过了一轮甲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