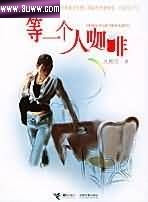上午咖啡下午茶-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丁之名,可以制茶,似与上文所说不是一物,况且友人也不说这茶喝了可以节育的。再查类书关于皋芦却有几条,《广州记》云:
“皋芦,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
又《茶经》有类似的话云:
“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茶饮亦可通夜不眠。”
《南越志》则云:
“茗苦涩,亦谓之过罗。”此木盖出于南方,不见经传,皋芦云云本系土俗名,各书记录其音耳。但这是怎样的一种植物呢,书上都未说及,我只好从茶壶里去拿出一片叶子来,仿佛制腊叶似的弄得干燥平直了,仔细看时,我认得这乃是故乡常种的一种坟头树,方言称作枸朴树的就是,叶长二寸,宽一寸二分,边有细锯齿,其形状的确有点像龟壳。原来这可以泡茶吃的,虽然味太苦涩,不但我不能多吃,便是且将就斋主人也只喝了两口,要求泡别的茶吃了。但是我很觉得有兴趣,不知道在白菊花以外还有些什么叶子可以当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山有栲”一条下云:
“山樗生山中,与下田樗大略无异,叶似差狭耳,吴人以其叶为茗。”
《五杂俎》卷十一云:
“以绿豆微炒,投沸汤中倾之,其色正绿,香味亦不减新茗,宿村中觅茗不得者可以此代。”此与现今炒黑豆作咖啡正是一样。
又云:
“北方柳芽初茁者采之人汤,云其味胜茶。曲阜孔林楷木其芽可烹。闽中佛手柑橄榄为汤,饮之清香,色味亦旗枪之亚也。”
卷十记孔林楷木条下云:
“其芽香苦,可烹以代茗,亦可干而茹之,即俗云黄连头。”孔林吾未得瞻仰,不知楷木为何如树,惟黄连头则少时尝茹之,且颇喜欢吃,以为有福建橄榄豉之风味也。关于以木芽代茶,《湖雅》卷二亦有二则云:
“桑芽茶,案山中有木俗名新桑荑,采嫩芽可代茗,非蚕所食之桑也。”
“柳芽条,案柳芽亦采以代茗,嫩碧可爱,有色而五香味。”汪谢城此处所说与谢在杭不同,但不佞却有点左袒汪君,因为其味胜茶的说法觉得不大靠得住也。
许多东西都可以代茶,咖啡等洋货还在其外,可是我只感到好玩,有这些花样,至于我自己还只觉得茶好,而且茶也以绿的为限,红茶以至香片嫌其近于咖啡,这也别无多大道理,单因为从小在家里吃惯本山茶叶耳。口渴了要喝水,水里照例泡进茶叶去,吃惯了就成了规矩,如此而已。对于茶有什么特别了解,赏识,哲学或主义么?这未必然。一定喜欢苦茶,非苦的不喝么?这也未必然。那么为什么诗里那么说,为什么又叫做庵名,岂不是假话么?那也未必然。今世虽不出家亦不打诳语。必要说明,还是去小学上找罢。吾友沈兼士先生有诗为证,题曰《又和一首自调》,此系后半首也:
周作人:关于苦茶(2)
端透于今变澄澈
鱼模自古读歌麻
眼前一例君须记
茶苦原来即苦茶
钟敬文:茶(1)
近来因为在山里常常看到茶园,不禁想说点与茶有关的零碎话儿。
茶树,是一种躯干矮小的植物,这是我早年所不知道的。在我那时的想象中,它是和桑槐一样高大的植物。直到两三年前,偶然在某山路旁看见了,才晓得自己以前妄揣的好笑。世间的广大,我们所知道的、意想的,实在不免窄小或差误得太远了。“辽东豕”一类的笑话,在素号贤博者,也时或无法免除的吧。
自然,物品味道的本身,是很有关系的;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日常应用的太普通了吧,喝茶的情趣,无论如何,总来不及喝酒风雅。这当然不是说自来被传着关于它的逸事、隽语,是连鳞片都找不出的。譬如“两腋生风”、“诗卷茶灶”,这都是值得提出的不可淹没的佳话。但我们仍然不能不说酒精是比它有力地大占着俊雅的风头的。举例是无须乎的,我们只要看诗人们的支籍中,关于“酒”字的题目是怎样多,那就可以明白茶是比较不很常齿于高雅之口的东西。话虽如此说,但烹茗、啜茗,仍然为文人、僧侣的清事之一。不过没有酒那样得力罢了。
吟咏到茶的诗句,合拢起来,自然是有着相当的数量的;可是此刻我脑子里遗忘得几等于零。翻书吧,不但疏懒,而且何必?我们所习诵的杜牧的“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虽然是说到茶的烟气的,但我却很爱这个诗句,并因之常常想起喝茶的滋味。“从来佳茗似佳人”,这是东坡的一句绮语。我虽然觉得它比拟得颇有些不类之诮,但于茶总算是一个光荣的赞语吧。不知是哪位风雅之士,把此语与东坡另一诗句“欲把西湖比西子”作起对来,悬挂在西湖上的游艇中。这也是件有趣味的事吧。
岭表与江之南北,都是有名产茶的地方。因为从事于探撷的工作者,大都是妇女之流的缘故吧,所以采茶这种风俗,虽没有采莲、采菱等,那样饶于风韵,但在爱美的诗人和民间的歌者,不免把它做了有味的题材而歌咏着。屈大均所著的广东新语中,录有采茶歌数首,情致的缠绵,几于使人不敢轻视其为民间粗野的产品。记得幼时翻过的《岭南即事》里面,也载着很逗人爱的十二月采茶歌。某氏的《松萝采茶词》30首,是诗坛中吟咏此种土俗的洋洋大著吧。就诗歌本身的情味来说,前两者像较胜于后者(这也许是我个人偏颇的直观吧?),但后者全有英文的译词(见曼殊大师所编著的《汉英文学因缘》Chinese—English Poetry),于声闻上,总算来得更为人所知了。
双双相伴采茶枝,
细语叮咛莫要迟。
既恐梢头芽欲老,
更防来日雨丝丝。
今日西山山色青,
携篮候伴坐村亭。
小姑更觉娇痴惯,
睡倚栏干唤不醒。
随便录出两首在这里,我们读了,可以晓得一点采茶女的苦心和憨态吧。
如果咖啡店可以代表近代西方人生活的情调,那么,代表东方人的,不能不算到那具有古气味的“茶馆”吧。的确,再没有比茶馆更能够充分地表现出东方人那种悠闲、舒适的精神了。在那古老的或稍有装潢的茶厅里,一壶绿茶,两三朋侣,身体歪斜着,谈的是海阔天空的天,一任日影在外面慢慢地移过。此刻似乎只有闲裕才是他们的。有人曾说,东方人那种构一茅屋于山水深处幽居着的隐者心理,在西方人是未易了解的。我想这种悠逸的茶馆生涯,恐于他们也一样是要茫然其所以的吧。近年来生活的东方化西方化的是非问题。闹得非常地响亮;我没有这样大的勇气与学识,来作一度参战或妄图决判的工作。但东方人——狭一点说,中国人这种地方,所表现的生活的内外的姿态,与西方人的显然有着不同,是再也无可怀疑的。
说到这里,我对于茶颇有点不很高兴的意态;倘不急转语锋,似乎要写成咒茶文来也未可知。还是让我以闲散的谈话始终这篇小品吧。有机会时,再来认真说一下所谓东西文化的大问题。
钟敬文:茶(2)
中国古代,似乎只有“荼”字没有“茶”字,——据徐铉说,荼字就是后来的茶字。这大约因为那时我们汉族所居住的黄河流域,不是盛产茶的区域吧。又英语里的茶字作tea,据说是译自汉语的。我们乡下的方言,读茶作“de”,声音很相近;也许当时是从我们闽、广的福佬语里翻过去的也说不定呢。
高濂的《四时幽赏录》,是西湖风物知己的评价者。他在冬季的景物里,写着这样一段关于茗花的话:“两山种茶颇蕃,仲冬花发,若月笼万树。每每入山寻茶胜处,对花默共色笑,忽生一种幽香,深可人意。且花白若剪云绡,心黄俨抱檀屑。归折数枝,插觚为供。枝梢苞萼,颗颗俱开,足可一月清玩。更喜香沁枯肠,色怜青眼,素艳寒芳,自与春风姿态迥隔。幽闲佳客,孰过于君?”(《山头玩赏茗花》)碎踏韬光的积雪,灵峰的梅香,也在高寒中嗅遍,去年的冬天,总不算辜负这湖上风光了吧。但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这文人笔下极力描写着而为一般世人所不愿注意的茶花。今年风雪来时,或容我有补过的机会吧。否则,两山茶树,或将以庸俗笑人了。——谁能辩解,我们每天饮喝着它叶片的香气,于比较精华的花朵,反不能一度致赏!
秦牧:敝乡茶事甲天下(1)
有人要编一本关于酒的文化的书,向我约稿,我敬谢不敏;而当有人要编一本关于茶的文化的书,向我约稿时,我就欣然应命。这倒并不是因为我想“抑酒扬茶”,而是由于我对饮酒是外行,而对饮茶之道则颇知奥妙,不但有话可说,而且介绍介绍觉得义不容辞。为什么?因为我的家乡潮汕一带,品茶的风气最盛,真可谓:“敝乡茶事甲天下。”我从小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下,自然对品茶就懂得点门道了。关于潮汕茶风之盛,可以从下面系列的故事中见其端倪:
故事之一,是关于因饮茶而倾家荡产的传说:有个乞丐到一门大户人家乞讨时,不要钱,不要米,而恳求给一杯好茶。主人是个品茶高手,就着人送一杯好茶到门口,乞丐品尝,却说:“这不过是很平常的茶罢了。”主人听了大惊,立刻吩咐妻子冲了一杯最好的茶,命人送了出去。乞丐喝后评论说:“这是相当好的,不过仍只能算第二等。”并问泡这茶的是不是某姓的娘子。主人听了更惊,就亲自到门前会他,盘诘之下,才知道这乞丐从前原是豪富。因爱好品上等岩茶(旧时最上等的茶叶,有卖到百两银子以上一斤的)而逐渐中落衰败,妻子也已离散,现在沦为乞丐,身上仍带着一个古老的茶壶云云。那个妇女,正好是现在这家主人续娶的妻子。主人震惊之余,只好呆望着这个乞丐飘然远去了……
故事之二,是关于茶家对水质的鉴别的。一个善于品茶的老妇命令她的儿子到某处山泉取水,泡功夫茶。儿子因嫌路远,就到附近朋友家座谈,顺便灌满一瓶自来水带回来。谁知泡好茶后,老妇一品味,立刻笑骂道:“小孩子欺骗老人,这哪里是山泉水,这不过是自来水罢了。”
故事之三,是关于以茶会友的。有个潮汕人出差到外地去,遗失了银包,彷徨无计的时候,漫步河滨,刚好见到有几个人在品“功夫茶”,便上前搭讪,要了一杯茶喝之后,和那几个老乡聊起茶经来。这几个立刻引为同调,问明他的困难后,纷纷解囊相助,并结成新交了。
故事之四,是嘲笑不会喝茶的人的。有个男人,买了好茶叶回家,要妻子“做茶”。妻子是外地嫁来的,不懂喝茶,竟把茶叶像烹制针菜一样煮了出来。那男人大怒,动手就打。吵闹声惊动了邻里,一个老太婆过来解劝,抓了一把煮熟的茶叶到口里,咀嚼了几下,不懂装懂地说:“不是还好么!只是没有放盐罢了。”那男人听了,才知道天下还有第二个不懂喝茶的人,不禁转气为笑,一场风波也就平息。
故事之五,是关于品茶师傅舌头的灵敏度的。“十年动乱”之前,一连有好几年,福建驻广州的茶叶公司每年都要请我们一批爱喝茶的人品尝一次各式名茶。那些泡茶的里手不仅擅泡茶,而且品茶更是术参造化。他们受雇于茶叶公司,负责评定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