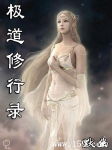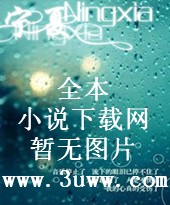传习录-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
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这分
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
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
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
也已。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向远近。凡有
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
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
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六如仇雠者。圣人有
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
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
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
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
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
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
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孝其亲,弟其
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
则人亦孰不能之乎?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
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
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
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
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
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
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
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葵、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
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哺育之愿,
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
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
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
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
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
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
… 页面 32…
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
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昌。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
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
内济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
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
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
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伤,
蒐猎先圣王之典章当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抚回
以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
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
墙,遂不复可睹。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
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
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戏谑跳踉,
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
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
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
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
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
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
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
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
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
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
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
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
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
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
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呜呼,以
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
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
有所必至矣!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
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
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
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
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主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于谁与望乎?
… 页面 33…
磨练于事上启问道通书
道通,姓周,名衡,号静庵,常州宜兴人。曾从学于王阳明,后又从学
湛若水,合会王、湛两家。曾历任知县。见 《明儒学案》卷二十五。
吴、曾两生至,备道道通恳切为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谓笃信
好学者矣。忧病中会不能与两生细论,然两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见辄
觉有进,在区区诚不能无负于两生之远来,在两生则亦庶几天负其远来之意
矣。临别以此册致道通意,请书数语。荒愦无可言者,辄以道通来书中所问
数节,略下转语。奉酬草草,殊不详细。两生当亦自能口悉也。
来信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来于先生诲言,时时体验,愈益明白。
然于朋友不能一时相离。若得朋友讲习,则此志才精健阔大,才有生意。若
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讲,便觉微弱,遇事便会困,亦时会忘。乃今无朋友相讲
之日,还只静坐,或看书,或游衍经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养此志,颇
觉意思和适。然终不如朋友讲聚,精神流动,生意更多也。离群索居之人,
当更有何法以处之?”
此段足验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无间断,到
得纯熟后,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
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尝病于困忘,只是一真切耳。
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能不
搔摩得。佛家谓之“方便法门”,须是自家调停斟酌,他人总难与力,亦更
无别法可设也。
来书云:“上蔡尝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
在学者工夫, ‘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的气象,一并
看为是。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 ‘何思何虑’,而忘
‘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堕于无也。须是不滞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
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
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何虑,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
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
虑邪?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下原自寂然
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
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
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以私意去安排
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虑”正是工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
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
说。既而云:“却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之论亦
是此意。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来书云:“凡学者才晓得做工夫,便要识得圣人气象。盖认得圣人气象,
把做准的,乃就实地做工夫去,才不会差,才是作圣工夫。未知是否?”
先认圣人气象,昔人尝有是言失,然亦欠有头脑,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
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此无星之称而权轻重,未开
之镜而照妍媸,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圣人气象,何由认得?
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
… 页面 34…
在我矣。程子尝云:“觑著尧,学他行事,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安能如彼之
动容周旋中礼?”又云:“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今且说通于道在何
处?聪明睿智从何处出来?
来书云:“事上磨练,一日之内,不管有事无事,只一意培养本原。若
遇事来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觉,安可谓无事?但因事凝心一会,大段
觉得事理当如此,只如无事处之,尽吾心而已。然仍有处得善与未善,何也?
又或事来得多,须要次弟与处,每因才力不足,辄为所困,虽极力扶起而精
神已觉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如何?”
所说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为学,终
身只为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得这一件,所
谓“必有事焉”者也。若说宁
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尚为两事也。“必